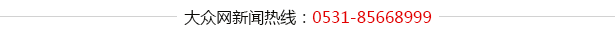衡诸古人,其擅画者往往擅书。盖笔力之刚柔,运腕之灵活,体势之变化,位置之安排,乃至神采之飞扬,全关乎用笔,这也正是古人特别强调所谓“书画同源”的原因所在。
学画者必须重视书法。书法不过关,画画这一关也过不了。对于一个画家来说,书法的成就往往决定其绘画的成就。
学书者当善择取。性情柔弱犹疑者,宜宗碑。因碑刻文字,书写者往往出之以庄肃端重之笔,韵高千古,力敌万夫,临之必受其益;而性情拘谨刻板者,宜崇帖,因帖多为简札,皆书者一时兴至,随意挥写,故自有一种闲雅潇洒之气,久临自可潜化气质。
贤儒之书醇雅,狂士之书奔纵,奇人之书历落,才子之书俊逸。
画跋不易为,它颇类诗前的小序,隽简有味,古人写时是很用心的。
而今之作画者多不能题跋或跋语不通。画文人画而不能“文”,岂不谬哉! 中国画为何讲究一个“写”字?具体地说,就是从整体上看是一幅画,
可从细部看,笔笔都充满着书法的意味。
隶书并不易为。若不从篆书入,终难有高古之象。
画竹不易,全从书法中来,故非书法成熟难臻高境;不少初学者往往不谙此理,虚费不少精力。
我觉得对于一个中国画家来说,书法是必修课。画中国画的,画写意画的,不练练字,那画什么写意画啊?至于我对我的书法,殊不敢自是。我收藏了的历代名家书法甚黟,很多书法,元鲜于伯机、王铎、傅山、董其昌、倪元璐,甚至吴昌硕、齐白石,都有。相比这些历代大师的书法,我觉得自己书法远未到位,愧对前贤。因此我很少送人字,每天还在坚持写字,因为这是个必修课。
最近看到周汝昌先生晚年背临的《兰亭序》,不胜惊佩。其时先生视力锐减,几近失明,作书只是凭习惯信手运动,而高怀逸韵,时溢笔端,非金丹换骨者,无此境界。周先生素以治红学而驰誉于世,本无心作书家,然观其书作,殊非时下颇负书名者所能比肩。仅此一端,足徵学养于书法之重要性,未可小觑也。
包世臣主张一本帖当临习百遍,然后换帖再临;而康有为则主张多读帖,碑刻经眼既多,源流自辩,然后择其精要,随意临写,真积力久,
自可“酿成一体”,康氏此说,颇合我心。
郑板桥、金冬心的卓异之处,就在于与专攻帖学的馆阁体迥异,他们重汉隶、魏碑,时人虽讥之险怪,但其毕竟能够独辟蹊径,自开新面,弃帖学之陈套,开碑学之先声,这就是郑板桥、金冬心书法的历史性贡献。
学书当先从篆隶入门,否则其趣不博,其意不古。大篆像规圆,隶像矩方;篆工间架,隶精笔力;习篆则可参结体之妙,作隶则可悟骨力之坚。故学六朝人书,若从隶入,尤得驾轻就熟、事半功倍之效。
近世书家,于右任之行草,吴昌硕之大篆,沈曾植之章草,皆为大家,允称巨手。至于康有为,开张有余,奇逸不足,凡掠捺处皆向上翘起,且转折无力,其书法与理论卓识殊难相符,殆亦如他本人所言,“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也。
中国画在宋以前极少落款,即使落款,也多穷款。逮至宋代,苏东坡、米襄阳等人文采过人,又擅书法,遂开于画上题款作长跋之先河。逮至元代以降,文人画大兴,如若在画上落穷款,则会贻讥士人,以为无学。至于清代,画面上长款、横款风行,这是因为清代画家大多既擅画、又工书法且精篆刻之故。
历代书评者,往往掺以先入为主的主观之见,不足凭信。如米芾便公然讥评欧阳询、柳公权的书法为丑怪恶札,颜鲁公的真书入俗品,徐浩的字肥俗无骨气。而对他自己的书法则自视甚高,以为胜过二王。此类怪评,皆以个人喜恶为审美准绳,纵使名家亦在所难免,为艺者切莫轻从。
在古代文人中,苏东坡的综合修养最高,诗、文、书、画、词、佛、道、禅、医、酒、茶、丹、烹、衣,无不精擅,后世鲜有能出其右者。修养既深,所诣自高,其书法得二王之神、颜鲁公之骨、李北海之势,且居于宋代四大家之首,大非偶然。苏东坡对自己的书法亦颇自负,书罢每留有余纸,要“留与五百年后人跋尾”。
康有为既强调“书贵有新理妙意”,又主张“学以法古为贵”,看似两相矛盾,但若将其置于“复古即解放”的历史语境之中,便不难理解。所谓复古,就是返本,就是自得,就是要破坏旧的价值系统,就是要从既定的文化框范中解脱出来,以通古今之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复古实即创新。
孙过庭所谓“偶然欲书”,最能达至“极工”。平生最忌“情怠手阑”
之时,偏偏有人索画,且不容稽延,立等而取。殊不知艺事有乖合之别,一涉匆遽,笔墨俱非矣。
康有为提倡运腕法,而包世臣则主张转指法,究以孰说为是,似难明断。沈曾植认为:“写书写经,则章程书之流也;碑碣摩崖,则铭石书之流也。章程以细密为准,则宜用指;铭石以宏廓为用,则宜用腕。因所书之宜适,而字势异;手腕之异,由此兴焉。”此真明达之见,为艺者自当用心体识。
书家达于极诣者,辄被推尊为“草圣”,却独不见有“篆圣”“隶圣”之称,其故何哉?盖篆、隶皆以法胜,易工;而草书则意多于法,必达至“放逸生奇”“神侔造化”之境方能下笔,故难工也。
草字自有法度可依,非漫无定规,随意而为。作草书忌笔飘而味薄,力轻而气浮,亦不能弩张剑拔,切齿裂眦。要重中和,明矩度,见阴阳,具变化。
唐代吴道子画江陵山水能一日而就,那必是草书所产生的极大效应;徐渭之所以能够开拓明代大写意花鸟画,也应归功于他那出神入化的草书。我在作《溪山无尽住烟萝》时,始终注重发挥草书的美感效应,那
种不拘一格、直抒胸臆的痛快淋漓,真令人心醉不已。
在《春雪漫空来》的画面上,漫天的大雪,通过草书意味强烈的笔墨挥写,恣性飞舞起来。她的飞舞,连同气的鼓荡,竟至使人产生山动的幻觉,这也正是我所着力追求的一种审美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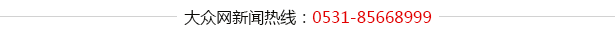
男是铁血硬汉女是铿锵玫瑰,穿防弹衣握枪,身手敏捷警车为伴...
好莱坞艳照门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此,好莱坞艳照门曝光...
9月21日,模特在展示旗袍。当日,由中国旗袍会主办、中国服装...
葬俗是人生礼俗的最终归属,是生命最后必不可少的程序,也是...
本书是一部批判中国食文化并带有追问、自剖、忏悔、既颠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