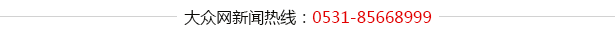(一)情真韵纯——李苦禅
当年李苦禅大师常说:“人品不高,落墨无法。”传统画家最看重人品、境界,因为东方写意绘画与画家的哲学观、人生体验大有关系。中国画一直在传承,也一直注重超越。历史上诸多大师的创作,都是对前一个时代的超越。比如潘天寿学八大山人,在笔墨上就有所超越;张大千、石鲁学石涛,在某些方面也有所超越。
每观苦禅先生的画,我总会想见其为人,总觉得以“情真韵纯”四字概括他的绘画艺术品质最为恰切——在商风日炽、物欲汹汹的时下,
这不啻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在当今的画家群中,似乎很少有人配享这一看似寻常的字眼。
苦老的那种人品,那种平易、豁达,那种真正的艺术家的傲骨,对我们的影响甚深。我觉得在我所亲炙的前辈中,苦禅先生是最突出、最杰出、最让人敬仰的一位。
通过与苦老的长期接触,我发现他作为艺术大师,一生总离不开一个“纯”字,纯真、纯洁、纯朴、纯正、纯粹、单纯。这是一种成熟的“纯”, 一种有深度有厚度有力度的“纯”。
“雪个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这是齐白石为李苦禅所作的品画跋语。“超纵”是形容李苦禅的画风:不为俗累,得道三昧,有一种质朴刚健、清新古雅的大美,其中不乏禅趣。而“肝胆”则是说李苦禅的人品:他一生笃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儒圣古训,又颇具侠骨义气,抗战时期倾囊资助革命,横眉冷对日寇,动乱年代保持铮铮铁骨,执教一生桃李满天下。在绘画题材上,李苦禅爱画鹰、鹫、鱼鹰、鹭鸶等猛禽大鸟,其代表作《河岳英灵图》通过综合、夸张等艺术形式,创造出雄浑生动的独特意象;其笔下“一洗万古凡羽空”的雄鹰,成为爱国精神、刚毅性格的象征。
苦老不仅追求诗书画印合一的境界,也突破了玩弄笔墨的阴柔格调,独创“金碧大写意”的画法,一开中国写意花鸟画雄浑豪放、阳刚拙健的新画风。其笔下,无论寻常的丝瓜藤蔓、荷塘秋光,还是古松虬枝、苍鹰白鹭,都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而他的巨幅荷花、劲节竹林、松崖群鹰,更是笔墨酣畅,充满雄浑博大的气象。晚年作品愈加返璞归真,雄健苍劲。
苦禅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首先是人品。苦禅先生在艺术上是至为
真诚的。一个人只要真诚就有力量。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坦荡也是一种力量,是胸中正气的外现。苦老在这方面堪称楷模,你跟他在一起,始终都会感到有一股力量,真诚、坦荡的力量。他讲的话,无一不是从内心发出;他画的画,就是他的“心画”。
我从苦禅先生游,给我最大的启发不仅在绘画技法,还有他对传统文化那种深刻的理解。我跟他学画的时候,他说,白石老人讲,“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即不要表面上去学,学老师,要学传统,要学中国历史。苦老到临去世前还在写碑写帖,还在伏案攻习。年轻时,我们常常去拜访老师,每当看到老师还在用心用力地临帖,我们都深受感动,那时老师已经八十多岁了。
(二)奇峰峻耸的八大山人
朱耷从一个皇室后裔一下子遁入空门,内心是相当痛苦的,行为也不免有些怪异,仅看他的款名就很怪异,既像哭,又像笑。其实,哭也罢,笑也罢,都是反抗现实的表现。朱耷作为一个皇室后裔,国破家亡,固然是大不幸,可对他的绘画艺术却又是大幸。巨大的隐痛内化为精妙的笔墨,再加上他学养深厚,人品高华,画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同凡响。
八大山人由儒而佛,由佛而道,凄恻彷徨,孤踪独往,内心里总守着一种孤独中的傲慢,表现在画上,就是极度的冷逸和清虚。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八大山人的悲惨境遇是互为表里的。因此我觉得,对八大山人的东西,不能死学。
我一向倾心八大山人。虽然他已经死了三百多年,可那只是他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其艺术生命仍如奇峰峻耸,令人仰怀。每当我看到八大山人笔下那些鹭鸶,透过它的眼睛,顿时进入到一种一尘不染的澄澈之境,它映照万物,创造着万物之间的诗性关联。三百多年过去了,可在八大山人笔下的鹭鸶眼里,却只是轻轻掠过的一个瞬间。细读八大山人的作品,总觉得那是一个奇迹,那是经过了艺术的升华,消解了纷繁与嘈杂之后所获得的一种单纯。这种大手笔、大气格、大境界、大简约,真要学起来,恐怕一辈子都不够哩。
(三)“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
如果从渊源上说,石涛早年即学梅清,后来跟梅清齐名,再后来又超过梅清。但我一看梅清作品,笔精墨妙,就感到石涛确实是“取法乎上”。
石涛尝谓:“古人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此言自当深铭五内。我曾长期生活在国外,每当埋首作画时,便感到“为有源头活水来”,脑际所翻涌的各种物象、意趣,就会纷纷奔来腕底,笔墨也能称其心之所欲言而任意驱遣;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有一种“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的快意,才发现真正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笔墨语言和抒情方式。
我在青年时代就很向往古人的那种隐士生活。石涛作品中所透发出的那种禅静,特别能唤醒我的诗性情怀。曾有人问我《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值多少钱,我说给我二十亿也不卖。
我平生最爱石涛,曾收藏他的十八件作品,其中最爱不能释的当推《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这是我十几年前在日本买的,当时花了一千万美金。这本《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是他用六年时间完成的,画中有四百多个人物,栩栩如生。石涛的人物画传世很少,现在存世的
有名的,除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香港一位著名收藏家收藏的之外,就是我这本册页。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曾感叹道,此物放在故宫都是镇馆之宝。《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画的当然全是罗汉,用铁线中锋画,每个罗汉身上的袈裟千变万化,极为丰富。
石涛的《石涛大士百页罗汉图册》,是其青年时期的作品。我敢断言:当代的所有人物画家,没有一个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将它临像。石涛的艺术足令我们现在的画家汗颜。
在如何对待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上,石涛提出“不似之似似之”这一重要论点。其中第一个“似”指客体,第二个“似”指主体。画家所创造的意象与自然往往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如是方能更加切合画家的审美感情,故云“不似之似似之”,这无疑是石涛在绘画理论上的一大创见,可不少人认为此语出自齐白石,这就未免“数典忘祖”。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就是对困难的攻克。石涛深谙此理,故提出“斩关”之说。所谓“斩关”,亦称“透关”,略合于当今的“闯关”“过关”之意。对于一个画家来说,从意存笔先至笔为我用,心手双畅,略无滞碍,这确实是一大难关,必须下狠心“过关”,不然的话,便如石涛所说,“若无斩关之手,又何敢拈弄,图苦劳耳”。
“入野看山时,见他或真或幻,皆是我笔头灵气,下手时他寻起止不可得,此真大家也,不必论古今矣。”石涛此言,未尝不隐含着他对自己“斩关”后以画笔驱遣自然的自许。有了这样的“笔头灵气”,便可超越古今,垂范千秋。
与“斩关”相悖逆的是“习气”。一向强调“法自我立”的石涛,对此深恶痛绝,曾指出:“今天下之画师,三吴有三吴习气,两浙有两浙习气,江楚两广,中间南都、秦淮、徽宣、淮海一带,事久则各成习气。” 所谓“习气”,就是自囿门派,死守成法,相沿成风;如此,必“死于法下”, 何来“笔头灵气”?
(四)别阔一新境界——张大千
张大千一生画过不少美女,但我觉得张大千对女性的欣赏品位不高,故笔下的美女不美,所画的古代仕女也缺乏“古典美”。而傅抱石画的美女就非常美,从色彩学上讲,黄皮肤、黑头发,非常漂亮。
转益多师是我师。我认为张大千真正的老师就是历史上的诸多名家。如果张大千只学他的业师李瑞清的话,就不会有张大千了。张大千最得力的是在取法于中国美术史上卓然而立的诸多大师。他二十多岁开始画石涛、八大山人,从这里入手,可谓“取法乎上”,自然比他的老师李瑞清高多了。
张大千最看重陈寅恪的一段话:“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阔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陈寅恪先生真解人也。对于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历来评论很多,其立志推尊敦煌文化的临摹之功,藉陈氏之定评,足可息争矣。
(五)一片童心——白石老人
画家们聚集在一起,常爱谈论的一个话题便是所谓“变法”,其实,所谓“变法”,重要的不仅是“法变”,而是“意变”。这一点,在齐白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齐白石所绘的兰花便可看出,他是一个极有个性的画家。古代文人在画兰叶时,往往追求飘逸一路、花姿舒展、花蕊吐露。但白石笔下的兰花却大为不同。叶子粗而健,花朵大而厚,健爽、厚重,令人一看便感受到郁勃的生命之力。这是人格化了的兰,是神化了的兰,是脱却前人窠臼的一种创新。
我曾听苦禅先生说,齐白石画虾须时,用一杆细细的笔,把笔尖顺直,从容画来,行笔非常慢,一笔不苟,虽细如发丝,而全身力到,绝不像外行人所想象的那样一挥而就。
齐白石专擅画虾,盎中常蓄小虾,观其潜浮跃动,此之谓“师造化”。
我们看齐白石七十岁后所画的虾,与他早年所画的已有很大的不同,早年基本上是如实画来,更像写生,质感和透明度不强,虾腿也显得瘦,
虾的动态变化不大;晚年他把虾须加多,加强了虾壳的质感和透明感,墨色也不像早年那样均一,笔先蘸墨,然后用另一支笔在笔肚上注水,这样就把虾的“透明”画了出来,虾一下子就活了。我们看大师的作品,应当尽力去体会其艺术上的变化和用心。
齐白石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怀乡情结的艺术家,他曾刻过两方印,印文分别为:“吾家衡岳山下”,“客中月光亦照家山”。很难说这都是些“闲文”,实为他本人自抒胸臆的第一主题。他一生写过许多怀乡诗,如:“登高时近倍思乡,饮酒簪花更断肠,寄语南飞天上雁,心随君侣到星塘。”又如“饱谱尘世味,夜夜梦星塘”“此时正是梅开际,老屋檐前花有无”等诗句,都是“夜不安眠”、“枕上愁余”所得肺腑之语。
他虽长年寄居京华,可满脑子都是湘潭亲人。一下笔,就是小时候熟悉的那些物象。这类作品,无疑是他的恋乡情结和童真情趣的自然流露。没有一点心机,甚至没有一点世故的渣滓。这正是我顶佩服他老人家的地方。
我最近看到齐白石画的那些小鸡、青蛙、蝌蚪、麻雀、老鼠之类的小动物以及果蔬之类的小品,那真是一片童心、一派天机。他实际上是把草虫花木拟人化、情感化、诗化,以至于把现实浪漫化。
齐白石虽无意以写实主义相标榜,但他始终精于体物,注重视觉经验;他并不以再现视觉表现的逼真为目的,而是注重把握对象的本质生命,始终遵循传统写意的形式语言,自觉地将传神、意趣和笔墨完美地结合,从而达至中国画传统的极境。
与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不同,齐白石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家,其成功之处在于:他在文人画家统治了数百年的中国画领域,以一个农夫的质朴之情、一颗率真的童子之心,运老辣生涩的文人之笔,开创出文人画坛领域前所未有的境界。在选材上,他则突破了单纯的民间画、学院画之间的森严界限,以一种历史上罕见的表现现实世界的热情,把绘画的主题转向乡心、童心或者说赤子之心,从而使他把作为农民画家的那种单纯质朴的天性在艺术上得到了最本真的表现。正因如此,齐白石不仅得到了传统文人阶层以及平民百姓的赞赏,也确立了其在画坛上的历史性地位。他的绘画充满了泥土芬香、生活气息,其作品既师造化又师古人,既有文人画的高致,又有民间艺术的朴华;他的画正是二者经过结合后升华的结晶。
明清以来,文坛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崇尚仿古,脱离现实,陈陈相因,玩弄笔墨,因袭前人的意境,毫无生气。这一点,“清四王”是有责任的。从这样一种历史语境来看齐白石的画,便不能不佩服齐先生的不蹈俗常、自出机杼、自树高格、自创新境!
真正的大艺术家往往具有极其强烈的个性,但这种个性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张扬,而是一种内在的弘毅和倔强,这一点在齐白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曾刻有两方印文为“木匠”“芝木匠”的图章,齐白石的难能可贵之处就表现在他从不讳言其木匠身份,也从不觉得他出身木匠有什么不光彩;而且他从来就不相信艺术是士大夫的专利,他就是要用他的笔墨,让那些士大夫从此不敢再轻蔑工匠。——这才是真正的个性!
(六)再谈吴冠中
吴冠中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他对待艺术的态度非常认真、执著。吴先生在艺术上有自己独特的主张,他将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写意文人画的某些观念和感觉方式,应用到了西方的油画上;同时又借着西方绘画特别是近现代绘画的某些观念和感觉方式,来表达中国传统绘画。他走的是中西合璧之路。很多人以为吴先生是一位反传统的画家,我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误解,我听过吴先生讲课,他并非不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他也很认真地研究石涛等传统文人画家的作品。实际上,吴冠中目前的主要成就是水墨画,如果不是他的水墨画,吴冠中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世界性反响;同样,如果不是他的油画,也不会产生吴冠中式的水墨画。
吴冠中在法国留学几年,应该讲是追求艺术的,但是他这个油画艺术很浮浅。他在中国学的中国艺术,也很浮浅。作品浅,认识也浅。正因为他的认识太浅了,所以他会说齐白石没有创新。齐白石怎么没有创新?齐白石无论在画上还是在书法、篆刻上,都是很有建树的。而中国文化是讲传承的,齐白石和谁一样啊?他学八大山人跟八大山人一样吗?他学石涛跟石涛一样吗?齐白石就是齐白石,齐白石的篆刻跟谁一样?近的跟赵之谦、吴昌硕不一样,远的跟秦汉印不一样,他怎么没有创新呢?
吴冠中的画由于缺乏深度,所以他的假画非常容易做。为什么?因为其画在技术含量上很低,文化上的底蕴很浅。但他的画很漂亮、很有个性,他也是这个时代产生的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可以看作是中国画发展百花齐放中的一朵小花,但不是主流。我认为,东西方文化应拉开距离,距离越远越美。用西方绘画来改造中国画,这种观念很难行得通。
吴冠中否定齐白石,其意在挖祖坟。因为齐白石有很多得意的学生,如李可染、李苦禅等等,各有建树;他把齐白石否定了,等于把很多人都否定了,也就等于把中国画给否定了。中国人否定中国画,就是数典忘祖。
若干年前,吴冠中提到“笔墨等于零”,固然大谬,但毕竟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学术观点。但他说的“100个齐白石赶不上一个鲁迅”,太荒唐了。事实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不管国家大小,历史悠久与否,他必须要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兹事体大,关乎民族尊严,何况我们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不可能没有主流意识。我们不可以用一种混乱的思维来否定齐白石,也不能用这种混乱的思维将鲁迅和齐白石强为轩轾。
吴冠中的不少言论,不但幼稚而且可笑。有一次我跟别人讲,陈丹
青有一句话挺到位,说吴冠中充其量是个文艺青年。虽然八十多了,思维是文艺青年。为什么呢?他两不沾,到了法国学点皮毛,回到中国画的画正好迎合一些无知者的口味。
吴冠中说:“我的艺术是混血艺术。”“混血”的概念究竟是什么?不言自明。所以吴冠中的这种思维,实际上是一个崇洋的思维。这种思维可以说是其来有自。我们知道,中国以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那时候知识分子基于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在文化取向上,所持的大都是一种激进的反传统的立场。胡适之就曾提出过全盘西化;鲁迅呢,则说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人吃人的历史。那么,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如所周知,早在乾隆时代,中国GDP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在乾隆以前,中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很多的发明都源自中国。当年马可波罗到中国来一看,啊,怎么纸能够成钱呢?都说在欧洲紫檀无大料,怎么没大料?都在中国呢!这足以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只看到中国衰弱的一面,看到鸦片战争一百年来的衰弱,被列强欺负。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短短的一百年,不能代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任何国家,不管历史悠久与否,不管强大与否,首先来讲应该是宣传自己的主流文化,这是一个民族自尊的问题。我们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为什么不让汉语将来在全世界像英语一样普及啊?以后你试试!所
以我就觉得吴冠中这种思维提得重点来讲,就是数典忘祖,是在刨祖坟。他否定了很多人,说徐悲鸿是画盲,说他要推倒中国画。就凭你吴冠中能做到这一点?我之所以要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深感他是有一定的名人效应,其画又卖得这么贵,对年轻一代很有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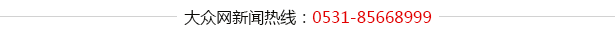
9月21日,广州单车爱好者推着自行车行经海珠桥。当日,广东广...
好莱坞艳照门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此,好莱坞艳照门曝光...
谢霆锋20日晚在四川参加商演,这也是他被曝出和王菲复合后,...
葬俗是人生礼俗的最终归属,是生命最后必不可少的程序,也是...
本书是一部批判中国食文化并带有追问、自剖、忏悔、既颠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