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爆发77周年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响起枪声,拉开中国全民族抗战序幕。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响起枪声,拉开中国全民族抗战序幕。

创造国内领先的营商环境,助推山东民营经济发展。

四年一度的球迷节日来了,准备好了吗?一起狂欢一起high吧!

征集一批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优秀漫画和动漫艺术作品。
关于纪念章,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山东团体协调人史鸣先生讲过的一个故事让人心酸。2012年9月,他在济南寻访到一位名叫张麒麟的远征军老兵,并为老人送上了一枚志愿者自制的纪念章。

最近一两年,作为一名记者,我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与“新”闻无关的事情上:辗转乡野,试图寻找挖掘段段被历史湮没的“旧”事。
我的采访对象总会以“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1937年……”开始。
接下来,必定要出现的字眼是:七月七日、卢沟桥。
移动互联时代,听见有人以“民国”纪元,恍若隔世。
但,无论时代如何“移动”如何“互联”,总也切不断与多半个世纪前的七月七日卢沟桥上的那声枪响之间的关联。
那个节点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走向,同时也改变了采访对象们的一生:从那个节点起,幅员辽阔的土地变得颤颤巍巍,弱不禁风,铁骑践踏,血雨腥风;也正是从那一天起,现今的老者当年的热血男儿,穿上军装毅然从戎,意欲用鲜血乃至生命守卫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遗憾的是,在横店影视基地“抗战神剧”的荒诞讲述中,我们根本无从得知那究竟是怎样的壮怀激烈; 在习惯宏大叙事的正统记忆中,我们很难感知身处其中的个体生命的温度与情感。
因此,我决定走进乡野村落,找寻仍然健在的抗战老兵,做挖掘个体抗战记忆的努力,用以对抗历史的遗忘。
2013年9月末,天气渐凉的时候,我完成了青岛抗战老兵孙树藩的口述整理。
几天后,按照约定,我将留存的一套样报寄给青岛的一位志愿者。随同快递一起寄出的,还有一件委托志愿者转交的特殊礼物——一枚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这枚金灿灿的纪念章,被装在一个紫红色的木盒里。
木盒上的暗黄色字体说明了纪念章的颁发单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内里的纪念章下方刻着的“1945——2005”,说明了它正常的颁发时间应是在2005年。
九九“重阳节”之日,恰是老人的生日。这天,老人的儿子将这枚纪念章奉上,作为老人的生日礼物——当然,老人并不清楚这枚纪念章的真正由来。
“见到纪念章后,老人泪流满面。”老人的儿子后来跟我说。
这枚于2005年问世的纪念章,于八年之后辗转送达老人手中——八年,恰恰是这个民族用以抵御外辱的漫长时光。
孙树藩是原国民革命军第32军141师721团卫生队的一名卫生兵,亲历过兰封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
在他的家里见到他时,老人正穿戴整齐地坐在沙发上等待我的到来。
彼时已近傍晚——这并不是一个跟九十多岁的老人交谈的最好时机。
这些年过九旬的老人在清晨或者上午与下午或者傍晚在记忆力和精神状态上,将会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种微妙的变化几乎与太阳的起落同步,在走访了众多抗战老兵之后,我发现了这一现象。
不过,孙树藩老人显然攒了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讲。我们用看起来略显怪异的方式交流了很长时间。
交流主要通过一块书写板进行:我将我的问题写在上面,老人捂着一只眼睛用另外一只视力较好的眼睛看清我的问题,然后给我讲述。待他讲完之后,我便擦去书写板上的内容,写下另外一个问题……
老人耳背的厉害,眼睛因为患有白内障而视力模糊。这是唯一能保障沟通的方式。
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从2012年底开始,在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山东团体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开始遍寻散落在城市与乡间的山东抗战老兵,为他们留存口述和影像,并将可整理成文的口述发表在报纸上,以期能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一群体。
陆陆续续,我们走访了四十余位抗战老兵,其中不少属于原国民革命军序列。
这几乎是这个拥有9500多万人口的省份,所能找到的散落于民间的全部抗战老兵——有时候,当我们或者志愿者按照线索历尽千辛万苦找到老兵居住的村落时,村里人常会惊诧地睁大眼睛:“你们找谁?!他死了都一两年了!”
这样的场景着实令人沮丧。
所以,虽然与孙树藩的交谈进行的异常艰难,却也叫人心生满足。
生活的磨难和时光的摧残,风干了不少鲐背之年的老兵记忆,也偷走了他们的表达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迄今只有二十几位老人的口述得以见报的重要原因。
作家余华小说《活着》里的一句话,时常回荡在寻访老兵的路途之上——“在这里,我常常听到后辈这样骂他们:‘一大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这些中下层军官或是士兵的一生从未被书写记载,不但不为公众,甚至不为儿女所知。“我还是头一回听他说这些事儿呢!”走访老兵时,我时常听到他们的子女这样说。
这也是我寄一枚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给孙树藩老人的原因。
那个晚上,在被问到余生最大的愿望时,老人在书写板上颤抖地写下了一行字:我想有枚抗战纪念章。
关于纪念章,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山东团体协调人史鸣先生讲过的一个故事让人心酸。
2012年9月,他在济南寻访到一位名叫张麒麟的远征军老兵,并为老人送上了一枚志愿者自制的纪念章。
三个月后,老人去世。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放置这枚纪念章的盒子已经磨损得非常厉害,纪念章也已失去了原有的光泽。
后来得知,老人每天不停的重复着一件事情:打开盒子,拿出这枚纪念章观看、抚摸,然后放回去,盖上盒盖。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竟把盒子的漆磨掉了许多。
所以,当孙树藩老人提出想有一枚纪念章的心愿时,我完全知道,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将老人的心愿写到了口述稿件里,但不抱希望。没想到,稿子见报的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电话是一位读者打来的。他看到了我写孙树藩老人的稿子,并在电话里明确告知,他可以送给老人一枚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以满足老人的心愿。
这位读者的特殊身份让我相信他并不是在开玩笑,这让我感到阵阵狂喜。
我知道,拿到这枚勋章的老人此生将再无憾,不后悔为这片土地所做的一切。
生于1921年的微山老人殷延伟,“七七事变”爆发时,正就读于当时的济宁中西学校。“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机轰炸济宁。因不愿做亡国奴,师生一行4人弃笔从戎,考取徐州十七军团学生队。后辗转陕西凤翔,经过重新考试后,进入位于西安王曲的黄埔军校七分校十五期步兵科,胡宗南任主任。
毕业后,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193师579团任团部见习少尉,后任91师272团第二营六连上尉连长。抗战时期,老人多次与日军交手。
部队在河南禹州与日军作战时,殷延伟被日军炮弹碎片击中,背部、后脑、颈部多处受伤,左嘴角被弹片豁伤,昏迷数日险些殉国。至今,老人的右耳后部仍有残留未取出的弹片。
老人如今生活在微山岛上的一个小村落里,家庭贫困,老伴去世多年。六十多岁的大儿子至今仍在岛外打工,小儿子平日里靠给人做小工为生。
我们前去看望他时,老人除每月100元的六十岁以上老人补贴外,无其他任何收入。
即使如此,提起早年的抗战经历,老人仍旧滔滔不绝,意气风发。对于能有人前去看望、倾听,老人心存感激。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老人说。
对于曾将生死置于度外的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冷漠和遗忘。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以纸张油墨为枪,打一场与篡改历史者的对抗战——在曾经是这个民族最坚硬的脊梁们面前,这一仗,不能输。每一块弹片,都是历史的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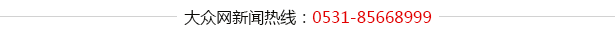
初审编辑:刘宝才
责任编辑:王雨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