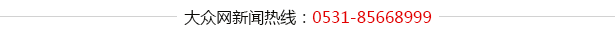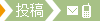山东最大书城万元征名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山东书城项目面向全国万元征名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山东书城项目面向全国万元征名

创造国内领先的营商环境,助推山东民营经济发展。

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变成美好现实

征集一批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优秀漫画和动漫艺术作品。
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曾跟在电影《少林寺》和《保密局的枪声》放映队后面走过家乡周边的许多地方,把这两部电影看了几十遍,其实这件事我在文章里讲过许多许多回,嘴都磨出茧子,但还是想说。

不消说,那时候我就梦想过现在这样的生活,或者说,在那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想看什么电影,就看什么电影,想怎么看电影,就怎么看电影。
出于对那两部电影的热爱,成年之后,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特别去了少林寺,还见到了《保密局的枪声》里刘啸尘的饰演者陈少泽,后来这都被写进我在《看电影》杂志的专栏里,自己还曾炫耀一样地配发了两首古体诗。
其一,关于《少林寺》的:
青山藏古寺,枯坐起岚烟;
黄鸟低飞近,上人已入禅;
风熏塔影斜,碧照诵经喧;
莫敢循声去,犹怀未了缘。
其二,关于《保密局的枪声》的:
铁胆铜魂一命悬;站来躺去两重天
风云一段堪挥洒,霹雳三枪传佳片。
乱世英雄重大义,有情无语对红颜;
新茶将问所何思,少校唏嘘叹老三。
人的矫情,是物质丰富的必然结果,从小我爸爸就常跟我说什么“礼义出于富贵”,活到现在,生活虽然离所谓富贵还差老远,倒也知足,赚大钱是要看天资的,人一生精力有限,这辈子若真能把小时候想过的日子过上了,便也算不白活一回。
为此,我就给自己立下一个原则,不写矫情的影评。
我清楚记得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人不再只看八大样板戏,而可以经常在俱乐部、礼堂和电影院里看到一些新鲜的电影时的那种兴奋劲头,自己并且一直对电影葆有那种兴奋劲头,唯恐把它们弄丢了。在这点上,有一人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他叫杜述铭,曾经的哈尔滨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年纪轻轻就被打成右派扫了十几年马路。1989年某件大事发生后,从大二进入大三的我百无聊赖,到《电影赏评》编辑部蹭电影看。那是个夏日下午,电影看罢,照例要讨论,但我是来看热闹的,却忽然听《电影赏评》的总编辑杜述铭操着山东腔的东北话喊:哈师大的段伟来了没有?段伟来了没有?我磨磨蹭蹭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答道,来了,我就是。
杜老师张着大嘴乐呵呵地跟其他的“影评员”们喊着,这个孩子的《晚钟》影评写得好啊,中文系大学生就是不白给,写得好!
那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篇算是影评的影评,名叫《晚钟:人道主义的弘扬》。
后来的事,正如我的师兄,哈尔滨日报记者申志远先生说的:
老杜的大背头,有点儿像新军刚剪了的辫子,人高马大的,说话声音洪亮,是一生未改的山东口音,大眼睛,脸上有好几块老年斑,长得有点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这个燃烧着生命激情的老人身穿一件黑色风衣,在80年代末阳光灿烂的正午,昂首阔步地从哈尔滨儿童电影院门前向我们走来,身后聚涌着一群由工农兵学商影评人组成的电影评论大军。那时管影评人叫影评员,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那是中国群众电影评论的盛世唐朝。杜老从小长在山东招远老家,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哈师大的学生司马平邦和我总能有幸在饭口跟他蹭饭,吃的多是山东包子和山东大菜的原因。
申志远记得多的是吃杜老家的大包子,而我记得多的是第一次在他家喝到了咖啡,还有,第一次在他的带领下,吃了一顿华梅的俄式西餐,还差点撑着什么的。电影,对我们这样的穷学生来说,不止有欣赏的快乐,还有点儿高级生活的滋味。
跟杜述铭先生混影评那段时间,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写影评,一边帮着编一本叫《电影赏评》的小杂志,在他老人家的指导下,我的一篇关于电影《野狼谷》的影评,第一次自发地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评论电影,也明白了电影其实是一门结构的艺术――不是吹牛,即使在今天,绝大多数成名成家的影评人,亦没达到过这样的深度。
正当我得意洋洋准备跟着杜老把影评进行到底的时候,就在我大四,在1991年春天的某一天,他突发急症昏迷不醒,不久便去世了,离世时刚刚60岁。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虽然,我的记忆力非常之不好。他把电影完美地安排进一个普通大学生的一辈子的生活里,让他比别人更早了解到拥有一个充满精神享受的世界是多么令人骄傲和满足。所以,现在每当我想起当年跟着杜先生囿于哈尔滨道里区一间小阁楼里自得其乐地编着影评杂志、聊着电影的过去式生活时,就总会有将自己现在的影评角度拉回到最初对电影的冲动。
我一直相信,每一部电影都是创作者心血的结晶,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都深深地刻着“热爱”两个字。所以,写影评时,其实我没兴趣对任何一部电影做细致到矫情、到变态的解读和评论,更不觉得影评人真有什么天经地义批判电影的权力,而更多是想通过自己的描述,与他人分享一部如此新鲜的电影,间或可以卖弄一下自己小小的某种成就感。
大概在1999年以后,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终于可以将评论电影作为自己的正当职业和正当生活,这之后我还参与编辑、策划了几本电影类杂志,可以天天边看电影边写影评。在我当上了一本叫《电影世界》的杂志策划人之后,晚上可能还因之梦里乐醒过来,不相信就因为自己看几部电影、写几篇文章就可以领到这样一份不错的薪水,把看电影当成自己的正当职业。
是互联网,对我的影评做了最认真彻底的“承认”――我知道,在所谓方家眼里,我的影评似颇不合乎影评规范,既不细讲剧情,也不注重分析表演,更缺少标准的要旨提炼,而只是以我自己的观点,更多的是司马平邦式的煽乎,把电影中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那一部分煽乎得更喜欢或更不喜欢,而不用写为电影或观众“负责任”的影评,或者说,我更在乎如何将影评本身写得更独立的意味和个性。
不过,亦令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当互联网(博客、微博客)给了我更宽阔的表达阵地之后,我却又自觉不自觉地给自己的评论套上“阶级性”或“民族性”的框框。曾几何时,影评界都以可以远离这两种“桎梏”为解放和自由,但今天我却不得不说,在我看来,自动自觉地在哪怕是电影评论中也流露出阶级性和民族性,是一种新的思想解放和自由,是另一种不得不面对的真实。不知你有没有觉得,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社会,已经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阶级化和民族化起来了。比如,我曾对李安的《色,戒》和陆川的《南京!南京!》发表过非常强烈的批判,强烈到前者的评论现在仍无法入选本书,现在看来,我仍完全接受不了一部站在反动于自己所认同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立场上的电影,哪怕是它的艺术水准真的有多么高、多么牛x。
我就一个自媒体影评人,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占山为王的愿景,我想这可能缘于我小时候听了太多如《岳飞传》《大隋唐》《水浒传》这种民间评书的缘故,也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
《影响剧大》这本书现在终于可以付梓出版,在此,还要深刻感谢出版社诸君的包容和认真。这些年来,或者因为在互联网上占山为王流氓成性,一直为现实的出版业所不容,几本带着强烈网络特色的时政评论和文艺评论集子都半路夭折,所以,这回算是如宋江一样终于得到了被招安的机会。
不过,我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山头的。
这书名若你很喜欢,它源于我女朋友周小白小姐的聪明才智,她也是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对象,真是一字千金呀,何况连本人都赠送给我了呢?还有,我的那一众几年前曾天天混在一起看电影、写影评的朋友,虽然在这自由散漫的互联网里生活下来,许多人从兴趣的趋同又渐渐萌生价值观的趋异,但电影永远是我们的最爱。更要感谢的,还有中国名博沙龙的朋友们,很奇怪的是,我们其实曾是一群生活兴趣迥异彼此陌生的人,是共同的价值观的趋同让我们越来越走近,越来越亲密。
回头想想,就在当年,我也只敢把看电影和写影评作为未来美好梦想的终极。故,以此为标准,我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生活已经超越了曾经的梦想。
2013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