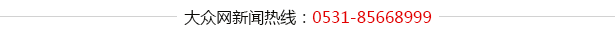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困惑与应对
曲阜师范大学 姜丽静 江娇娇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深刻宏大的社会变革进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整体的发展过程,社会转型一般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换、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1]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转型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在前近代时期,由于人文知识和政治权力的有效结合,使得具有“人文知识分子”特色的“士”位居四民之首,处于社会的权力中心。然而,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持续改革和变迁,知识分子的地位、角色和职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知识分子原有价值观念的冲突。此外,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主要表现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却面临传统道德的迷失和朴素人文关怀的式微这一突出矛盾和问题。当前农村社会的道德衰落和信仰迷失恰恰为人文知识分子直面社会危机,结合专业特长,开展深入研究,重建信仰和价值体系提供了历史舞台。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特征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由传统社会的“士”转化而来,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与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与转型的重要标识。中国传统士人历来有着“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传统。近代之后,随着科举制度与封建帝制的相继废除,士大夫阶层丧失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开始日渐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并逐渐向知识分子过渡。与传统士人相比,近现代知识分子体现了一种“天职感”与“志业感”交互混杂的特点。[2]具体而言,近现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士人那样直接进入国家的权力中心,借助行政权力用长期的“学”所把握的“道”来治平天下,而是退居学院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主要通过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来启蒙民众,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并将对社会和家国的深沉关切寄予于学术研究之中,从而有效实现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专业性与公共性的有效结合。
因此,虽然传统士人与知识分子的含义不尽相同,但传统士人“社会承当”的精神传统却被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下来。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特征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实用主义逐步替代政治权威主义,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地位、角色、职能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活动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此导致了知识乃至整个文化的裂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导致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易位,人文知识边缘化。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与精英文化的衰落。这些变化对当前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改变了科学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改革开放前,中国传统上国家意识由人文知识与政治相结合而成,科学技术则相对处于边缘地带。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更强调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性,掌握科技的知识分子进入相关政府部门,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而那些探索人生意义和价值等领域,提倡终极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则滑入社会的边缘地带。其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极大冲击了知识分子原有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冷落,甚至造成部分知识分子人格追求的迷惘。 [3]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质与突出问题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面性
20世纪90年代左右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开始在我国流行,并得到了深入的发展。我国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社会转型”:一是社会形态变迁,主要指我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二是经济体制转型,主要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和自然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三是发展模式的转型,主要指由目前单一的、粗放的发展向科学发展的模式转型。[4]
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势必触及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复杂因素,从而引发民众在心理和行为上的诸多不适应和不满意。这些不适和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极有可能累积为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冲突。[5]其集中表现为“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6]比如城乡问题、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利益格局、文化传统等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均显示出这种社会结构转型的两面性。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突出问题:农村社会转型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与否,关系到我国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社会转型是指“由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小农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农村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型过程。”[7]据此,在一定意义上,农村社会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成为制约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改革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后,农民的眼界逐步放开,抓住机遇的小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很多农民则成为经济上的落后者。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乡镇企业和“打工潮”的涌现,一方面极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则导致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外流与农村内部社会阶层的分化。“农村内部传统权威的作用被侵蚀,农民之间的依赖关系极大地弱化了。农村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也伴随着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扭曲和摧毁。”[8]换言之,在农村,由伦理关系维系的集体价值观逐步被个人主义价值观所替代。其间,由于个人行为有效约束机制的缺乏,又导致各种扭曲现象的出现,如农民趋利性日趋明显,价值取向日益多元,但价值判断却失去参照标准,等等。[9]其结果是,农村社会原有的朴素的人文关怀在当代世俗取向的大众文化中日益衰微。
三、农村社会危机中知识分子社会承当精神的继承与实现
“任何社会的全面转型必然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巨大调整,社会各阶层的权力与利益、地位与作用也会有剧烈错动。”[10]
事实上,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在对知识分子和农村社会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农村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人文关怀的衰微恰好为边缘化的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致力于价值体系的重建和信仰培育。因此,面对农村社会转型的困境,人文知识分子理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转换身份,结合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实现自身和农村社会的双重转换和转型。
(一)在人文与科学的冲突中寻求和谐共存
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知识价值的评价标准、实现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在现代经济建设中,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认识不断地深入人心,以及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巨大经济价值的显现,导致了人文价值和人文信仰的不断淡化。实际上,社会系统是由其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密切相关的子系统构成。这三个子系统的作用相应地表述为:“政治为人民争取权力,经济向市场追求效益,文化则是意义的领域,负责替人类的历史行为和现实活动提供解释和确立价值。”[11]文化的缺失,人文信仰的衰落,很可能为社会的协调发展留下慢性发作的内伤。实际上,人文精神所关注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以及人自身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而科学技术主要关注的是对人与物的控制及其实效。[12]由此看来,两者的价值目标大相异趣。
应当注意到,虽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诉求,但是,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相比,精神文明的衰落和价值体系的崩解则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13]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知识分子能顺应我国社会转型,特别是农村社会转型的实际,凭借着对科学技术的掌握,不仅在发展农业、增进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等问题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还为自身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尊重。而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乃至转型中整个中国价值体系的崩解,恰恰为人文知识分子在结合现实实际,秉持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提供了引导社会重建价值体系和重塑人文信仰的必由之路。
(三)在价值多元的冲突中坚守终极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基本的价值取向较为稳固,没有太大的冲突。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集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于一身,具体可表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也是与当时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即社会主义政治理想与集体主义道德理想的统一一致。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活动中心向经济的转移,社会价值取向的日益多元化。尤其是社会上经济利益至上以及个体价值的凸显等价值追求,不仅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冷落,“精英文化”的衰落,更极大地冲击了知识分子原有价值观。[14]
实际上,“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视为‘社会良知’,指的是他在社会功能上的标示,亦即永远地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与捍卫,对人类公益事务抱持强烈的人文关怀,并诚恳地视之为自己不可推卸、不可转让的职责所在,只有二者齐备一身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形象。”[15]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经济、社会资本日渐重要,知识分子需要在坚守终极价值观的基础上,以温和的姿态来面对社会大众的多元价值取向,正视社会主导价值观的缺失,在整合科学理性、人文精神和集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并存的价值观体系,[16]并对世俗文化加以合理地制衡。就人文知识分子对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的介入来讲,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分子与农村社会之间构建一个必要的缓冲,方有可能真正深入并正确引导农村社会的转型。
参考文献:
[1] 杨发祥,林晓兰.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心态[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9,(3):77-82.
[2] 姜丽静.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5.
[3] [12][14]范竹增.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人格[J].社会科学战线,2001,(4):223-227.
[4] 郑佳明.中国社会转型与价值变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1):113-126.
[5] 李宏斌,钟瑞添.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内容、特点及应然趋向[J].科学社会主义,2013,(4):139-142.
[6] 杜玉华. 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65-71,154.
[7] 王冰.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模式、特征和趋势分析[J].经济学家,2007,(4):97-102.
[8] 陈长江,高彦彦.农村社会的转型困境与基于正式制度的破解[J].农村经济,2010,(3):82-85.
[9] 杨春娟. 农民道德观念变迁与道德提升路径选择[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5):9-13.
[10] [11][15]张岩泉.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三题[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1):1-6.
[13] 贺照田.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J].读书,2014,(7):20-28.
[16] 姜锡润,王曼.论社会转型时期价值冲突的根源与价值观重建[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8(2):149-155.
(本文作者 姜丽静:曲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与文化、高等教育史研究。江娇娇:曲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教育史、比较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