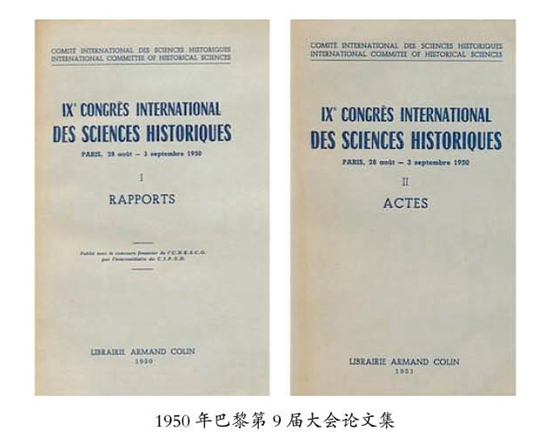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l950年在巴黎召开了战后第一届大会。但是在巴黎大会之前,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恢复活动和人事变更情况。
苏黎世大会之后,连续两任秘书长拉里提埃尔和莫雷都是改革派,他们都试图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提高大会的效率,通过改组大会机构使之朝着更加实体化的方向发展。但造化弄人,拉里提埃尔因战时与纳粹德国的合作而沦为通敌者,身败名裂;莫雷的激进主张开罪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元老们,结局是他在1950年的巴黎大会上引咎辞职、黯然下台。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再赞助国际史学会,史学会的组织机构也朝其他方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38年,拉里提埃尔连任秘书长之后,认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日常性的国际史学项目研究,当前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办会上了,应该进行改革。他对《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公报》的工作也不满意,这份刊物已出11卷45期,主要内容是会务工作和文件,缺乏科学性。苏黎世大会之后,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编纂《公报》。
苏黎世大会之后,捷克邀请国际史学会1939年在布拉格召开全体委员会,但是1939年4月,纳粹德国已经占领了捷克全境,全体会议改在卢森堡举行,讨论是否接受意大利召开下届大会的申请。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意大利已经建立了法西斯体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科特、田波烈和丹麦、比利时的史学会都反对在罗马开会,但利兰和拉里提埃尔本着大会应该超越政治分歧的理想主义愿望,还是接受了邀请。好在二战的爆发使大会避免了这样一次难堪的经历。
1940年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菲利晋·贝当元帅继续留在法国本土并出任政府总理。贝当政府旋即宣布投降,把政府所在地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故这一时期的法国政府称维希政府或贝当政权,是德国占领下的傀儡政权。
在巴黎的国际组织大多逃至美国,但拉里提埃尔的秘书处继续驻留,他寻求在德国当局和维希政府的支持下工作,事实上他如愿以偿。利兰决定,为了不让历史学家的国际大家庭分裂,战时不再办会,也停止给巴黎的秘书处提供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他把这笔钱都用于资助来美国的欧洲史学家。副主席、英国的韦伯斯特对此持赞同意见。
拉里提埃尔编纂了《公报》第46和47期,作为第12卷的前两期。因战时无会,《公报》主要是收入学者的论文,其中不乏这位秘书长本人的论文。他的主要联系人是德国研究所所长卡尔·埃普廷,埃普廷长期在法国生活,熟悉法国文化和学术界,战时做了许多德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事青,拉里提埃尔也组织过德法两国历史学家会议。期间曾有提议把秘书处迁至柏林,但因德国历史学家的反对而终止。
战争结束之后,拉里提埃尔被停止教职,法国史学会认为他不再适合做国际史学会的秘书长。利兰从大洋彼岸来信,敦促他去职。1945年11月,利兰致函执行局的其他成员,建议召开史学会全体会议,商定下届大会事宜。法国史学会新任主席是罗伯特·富提埃尔,他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1942年曾被纳粹判处终身在集中营监禁,他的经历使他享有崇高的威望。富提埃尔在给利兰的信中,提名查尔斯·莫雷为下任秘书长,莫雷是年轻一代的学者,极富朝气和理想。
利兰,这位国际史学会的创始元老和大会最真挚的支持者,这时的想法起了变化。他婉拒出席1947年6月3日至5日在巴黎郊区罗伊蒙特召开的会议,并且辞去主席一职,请诺布豪兹担任临时主席。任何人都不知道利兰的心事,迄今为迷。事实上,利兰以后再也没有参加过一届大会。埃德曼作了推测,认为利兰不愿看到国际史学家之间的分裂,他援引利兰的书信:“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要务是把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聚集到友好而有益的合作中,不要做任何增加这方面困难的事情。”利兰是一名高贵的人类大同的理想主义者,他超前的国际主义思想注定是孤独而寂寞的。
1947年,在罗伊蒙特举行的国际史学会执行局和法国史学会的联席会议讨论了四件事:国际史学会的科研工作、人事变更、如何处理战败国的史学会的会员资格和确定下届大会主办地。
在史学会工作方面,《公报》停刊;《历史学国际书目》外交官名录和宪政史研究的工作继续进行。在人事方面,诺布豪兹任代主席,莫雷任代秘书长。在战败国史学会的资格方面,布鲁塞尔大会敌对的一幕不能重演,决定意大利、奥地利和西班牙史学会的会员资格保留,下届大会重新接纳德国和日本。富提埃尔表达了法国政府希望1948年在巴黎召开大会的意愿,这年是法国1948年革命100周年的纪念,大会将富有意义。国际史学会副主席韦伯斯特和司库伍德沃德都强烈反对这一提议,韦伯斯特的理由是基于“革命的政治特征”。伍德沃德说:“战后首次大会就以这种方式和政治联系起来,是不科学的,是很不明智的。”在表决时,只有法国、瑞士和比利时赞同。会议决定下次大会1949年或1950年在法国召开。
另外,执行局主动对不同社会制度的苏联示好,为苏联留出一名执委职位,但苏联方面没有回应。埃德曼称苏联是“装聋作哑”。这只是一个开始,国际史学会在战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争取东欧国家的历史学家参加大会。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重大组织变化是,它不能再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赞助,转而求助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并且国际史学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委员会(ICPHS)的成员。
莫雷对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设计理念和他的前任拉里提埃尔相似,主张把委员会办成一个国际历史学交流中心,成为一个研究实体,这点也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认同,但是,执行局的元老们对自己旧日的政绩还是很满意的,在1945年召开的国际史学会全体会议上,冈绍夫和伍德沃德辞职,表示不能与莫雷共事。主席诺布豪兹称,下届大会他就卸任。既然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莫雷只好停下改革,也表示下届大会辞职。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停止了对史学大会的资助。这样,国际史学会只好再找新的施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答应支持,但是,前提是要加入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委员会。富提埃尔在国际史学会全体会议上,反复保证此举丝毫不会损害国际史学会的独立性。
1950年的巴黎大会有来自33个国家的1400人参加,但是没有东欧和德国学者。
巴黎大会通过了四项具有制度性变化的决议。第一,就是正式加入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委员会,且成为历史类的唯一会员,以后任何历史组织都必须通过国际史学会才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联系。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成为一项规则,例如,2010年成立的全球世界史学会就是通过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全球世界史学会当时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部分与会。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对世界全球史学会的到来很重视,并在会议议程手册上突出了其位置,承认世界全球史学会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分支机构,支持其参与 2015年济南大会的筹划工作。世界史学会还通过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二件是确定国际史学会总部和司库驻地都设在洛桑。以前总部随司库走,先是跟利兰设在华盛顿,后是跟伍德沃德设在伦敦。现在改为常设洛桑,因为瑞士金融发达,且为中立国。
第三件是决定秘书处继续常设巴黎。因为秘书长莫雷在这届大会辞职,新的主席富提埃尔提议秘书处常设伦敦。但遭到英国副主席韦伯斯特婉拒,他说:“如您所知,秘书长应该精通法语,英国很少有人符合这一条件。如有可能,秘书处还是设在巴黎。如果不在巴黎,那就设在布鲁塞尔。”最后决定继续设在巴黎,47岁的米歇尔·弗朗索瓦成为新任秘书长。
第四,是吸收专门性的国际学术组织加入国际史学会,这些专门性的组织的地位与各国史学会的会员资格等同,在大多数事务方面具有投票权。
为了纪念马克·布洛赫这位年鉴派的创始人,1950年巴黎大会的主题之一是“事件是否是历史研究必要的中心内容”。马克?布洛赫在二战时期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被捕后于1944年被枪杀于集中营。因为在第一代年鉴派看来,传统史学就是政治事件的历史、历史主义的历史和叙事的历史,传统史学是年鉴派的批判对象。
二战之后,除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外,西方新史学的流派主要有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克里奥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纳米尔学派,新史学借鉴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数学、控制论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并且使用电子计算机工具,史学领域从政治史扩张到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心理领域,研究的人物除社会精英之外,把芸芸众生、普罗大众包括在内,使用的资料几乎无所不包。史学大会所折射的就是这样一部西方史学史的演进状况,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以年鉴派为代表进行择要介绍。如国内学者所言:“年鉴派是新史学中最有影响、因而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此,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条件地把年鉴学派的范型视作新史学的代表未尝不可。”(陈启能主编:《八个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年鉴派的创始人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1946年改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化》,1994年又更名为《年鉴:历史学、社会科学》。巴勒克拉夫评论年鉴派说:“新历史学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广为接受,其关键所在,或其特征,就在于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开拓新的视野。” (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2-63页)这样,年鉴派的学术地位与其说来自其研究成果,不如说是它的方法给历史学带来的活力。年鉴派的探索解放了历史学家蓄存的知识和能力,因而得到了同行的推崇。
年鉴派创立之初,布洛赫和费弗尔就提倡研究“总体史”,这不同于传统的政治事件的历史。在时空观念上,年鉴派研究的不是单线的时间,而是不同文明各自的时间以及同一文明之内的不同时间,在空间上突破了传统的以国家划分研究对象的框架,代之以区域和全球范围。布罗代尔进一步提出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的概念,分别对应着“结构的历史”、“势态的历史”和“事件的历史”,历史中的人也从个别的精英扩展到群体的大众。研究对象的扩大带来了史料类型和数量的增加,而处理这些史料又需要引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年鉴派就这样带来了历史研究的连锁反应。
巴黎大会组委会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年鉴派人物:富提埃尔、莫雷、费弗尔、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国际史学会执行局也同意大会的参加者按照“年鉴派”和“传统派”分野,但如何组织由法国人来定。埃德曼说,“新史学”就是该方法支持者的自称,他们把新史学定义为历史主义或事件史的反义词,“以此设定,巴黎大会的论文就是用来检验他们对于新史学和历史主义二者区别的理解的”。
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和皮埃尔·维拉参加,值得注意的是,维拉还是《年鉴》杂志社的成员。大会的分组划分也显示了新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人类学和人口学”、 “观念与心态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制度史”,还也设了一个“历史事件”分组。年鉴派阵营的参加者除法国人外,还有意大利的奇波拉、英国的波斯坦、比利时的敦特、美国的德·鲁福尔和西班牙的萨波里,大会的约一半发言都是由年鉴派所作。年鉴派的发言有的比较平和,也有的很激进。弗耶斯·雷诺阿德说:“政治史只是现代史学的研究目标之一,也是最不值得投入的一个,现在它已是历史最陈旧的形式了。”而埃克尔·德斯·查迪斯的发言显得咄咄逼人:“当所有的王侯的文件都被出版或编目,当日期、事件的后果、条约、国家和政府的领袖都被毫无争议地决定了的时候,当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家的历史都以学术方式连贯地书写出来的时候,政治史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未来的历史学家依赖前辈的成果,再也不要动它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可以砍掉这个多余的成分。”
显然有的年鉴派走向了极端。对年鉴派的批判既有来自传统史学的,也有其他的新史学家。新史学家、法国的皮埃尔·莱诺文在点评莫雷的发言时,针对年鉴派重视社会经济史的经济决定论,提出这种论点不足以解释相同经济状况的人们为何有不同的社会行为:“经济发展不能解释一切。例如,不能解释法国有相似经济利益的社会群体为何在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同的行为?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被不同信仰所区别开的吗?在对两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是否有人注意到相同类型的社会力量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行为?完全依据经济和社会力量,能够解释中欧和东欧少数族群的整体运动吗?这些力量在某个地区发挥影响力是显然的,但少数族群除了对他们的物质利益进行政治抗议,是否还有其他的事例?”这是对新史学的早期质疑。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魏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