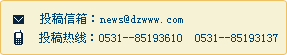“中国最美女诗人”翟永明:诗歌濒危 诗人寂寞
2010-12-26 15:10:00 作者: 来源:羊城晚报
| |
翟永明:诗歌濒危 诗人寂寞
据说她是中国最美的女诗人
她开酒吧讨营生,亦是为了获得跟社会接触的机会
她近十年来的诗歌,总是充满男人般的批判力量
翟永明(1955- )
祖籍河南,出生于四川成都,知识分子写作诗群代表诗人之一。1981年开始发表诗作,1984年完成了第一个大型组诗《女人》,其中所包括的二十首抒情诗均以独特奇诡的语言风格和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了文坛。该组诗在1986年《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发表之后,更是引发了巨大的轰动,1996年出版了散文集《纸上建筑》之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现居成都写作兼经营“白夜”酒吧。作品曾被翻译成为英、德、日、荷兰等国文字。在数十年的诗歌写作中,翟永明一直保持充沛的写作和思考的活力,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在中国诗坛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
一则新闻报道成就一首好诗
何言宏:你早期的诗比较“个人”、比较“自我”,现在的作品却有明显的社会性,但我觉得,你与社会的紧张一如既往的。
翟永明:现在我写的东西,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是表达个人感情。但是诗的触角已有很多是跟社会问题有关的。比如说2002年写作的《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这首诗就来源于一篇新闻: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被拐卖到了妓院里面,小女孩只有十三岁。但是,三个月内,共有300多个男人以嫖客身份强奸了她。说“强奸”,是因为这个女孩完全是被迫的。小女孩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她只好在算术本上记录了那些人。那些人都没有名字。她只是记下了多少个,今天是哪一个,明天是另一个。后来,等她的父亲终于找到她,是三个月之后,她已经得了十几种性病,并被切除了卵巢。她的父亲哭着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每个人都有女儿,我的女儿那么小,那些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看了以后,触目惊心。对我的震动特别大,我觉得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完全没有概念。为了满足自己最私欲的要求,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但这样的题材我以前完全没有写过,它跟现实这么紧密,直接就是一个新闻。我从前觉得新闻是不可能直接写成诗歌的,诗也应该远离社会新闻以保持自身的诗意。但这个报道对我刺激特别大,我后来觉得还是要用我自己熟悉的语言来呈现。在写的过程中,我一边写一边就把我的疑虑写进去了。这首诗中的思考实际上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这个消息对我的触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涉及诗歌的写作本身:我们今天的写作,是不是应该涉及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应该和社会发生那么直接的接触?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我这样写,是不是把我的诗歌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了?
何言宏:这些年来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作家和诗人都从新闻当中寻取题材,作家当中比如余华,据说他的《兄弟》就是取材于新闻报道。还有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是取材于一个罪案报道。其实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很正常,关键是怎么处理,当然对诗歌来说,面临的问题可能更特殊。对了,有一本法国人写的书,叫做《杂闻与文学》,非常有趣,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过它所讨论得更多的是小说和戏剧。现在的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中国新闻”,真的是我们文学的一个重要资源。
翟永明:后来出现的贵州习水糟蹋幼女案的结果,已杳无音信,再后来的丽水强奸女生案似乎也没有引起网民们强大的关注。而且,“强奸”在法律上变成“嫖幼”,也就是在把责任往女孩身上推。这不仅是强奸女孩,更是强奸公众的智商。记得《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这首诗在《诗刊》上发表时,题目被改成《部份的她》。也许,《诗刊》的主编也觉得“雏妓”二字太过刺激人的神经了。
何言宏:他是否觉得“雏妓”这样的字眼会损害“诗美”?!
翟永明:当代诗歌的写作中“美”是有多种含义的,此外,当代诗歌也不能仅仅是“美”的欣赏者。当代人的情感也不仅仅是风花雪月。这一点,一个诗人应该清楚。我早就不会用字面意义上的“美”来定义诗歌的好坏。同时,我觉得对现实的观察,有时对诗歌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对诗歌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你跟这个社会的接触,也会导致你的写作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我想这首诗是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好诗我没有把握,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对我的诗歌观念变化所起的作用。所以,我本人很喜欢这首诗。
何言宏:我也喜欢这首诗,我以为它应该是你这些年来的代表作之一了。像《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这样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的作品,每一位熟悉你的读者读了它后,都会对你有新的认识,会有一种惊异,也会心生敬意。
翟永明:我目前的写作中都希望诗歌与现实有一种更紧张和更明确的关系,当然,必得是一种诗意的方式。一种现代的诗意,不是过去那种纯抒情的诗意。
诗人的其他营生
何言宏:近十年来,除了写诗之外,主要还做什么?
翟永明:这些年我最主要的经历除了写作之外,就是开了“白夜酒吧”。
何言宏:为什么会想到开酒吧?
翟永明:我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但中国稿费太低,所以对于我来说,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我一直向往的。因为这一念之想,我开了“白夜”酒吧。当然,“白夜”只是我的一个生存背景,我赖以生活的地方。而更为重要、更吸引我的,依然是写作。我一直认为,作家如果有其他营生,只会给他的写作提供一个开阔的视野和观察社会的机会。
何言宏:“白夜”已经成了成都的一个著名的文化景点了,人们去成都,宽、窄巷子一定得去,去了宽、窄巷子,“白夜”更得去了,但它是在宽巷子还是窄巷子?
翟永明:窄巷子。十年来,“白夜酒吧”聚集过诗人、艺术家、媒体人、艺术爱好者,也举办过若干小型寒碜但个性张扬的签名售书和一些艺术活动。诗人们也常常在这里举办朗诵会,“白夜”让我的写作视界和对现实的理解都大大地打开了,并且让我的写作发生了很根本的变化。从1998年到现在,我的写作可以说是非常自由和多变,这在很多时候都与我关心的事情发生改变有关。我认为作家的写作应该跟随内心,内在的思想和观念变了,写作一定会变。这些年我出了两本诗集、三本随笔。其中《白夜谭》完全是记录“白夜”和“白夜”周边的艺术群体。
何言宏:经常会从一些朋友那里听说“白夜”举行的各种活动,“白夜”已经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史和艺术史的重要见证。你说“白夜”的很多活动“小型寒伧但个性张扬”,和咱们诗歌相关的这些活动比如有哪些?记得你还主持策划过诗歌节。
翟永明:那一届诗歌节发生了很多变故。我在这件事里也太天真,处事太幼稚。以为用民间的资金做一个比较纯粹的诗歌节,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不考虑官方的、体制内的关系,绝不邀请某些自以为掌握了诗歌权力的人。但我确也没想到那些人会有这么大的破坏性。诗歌节被取消了,但从美国过来的两位诗人却已经来中国了,同时不少外地朋友也已买了不能退的机票,他们仍然来了成都。所以,后来我只好临时又安排了在“白夜”的诗会,从一个公共空间的诗歌节变回了一次诗人的小型聚会。
何言宏 (来源:羊城晚报)
陶云江

更多新闻
相关阅读
您对其他相关新闻感兴趣,请在这里搜索

自定义搜索
> 进入微博< 热点图片
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
2、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大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3、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大众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
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