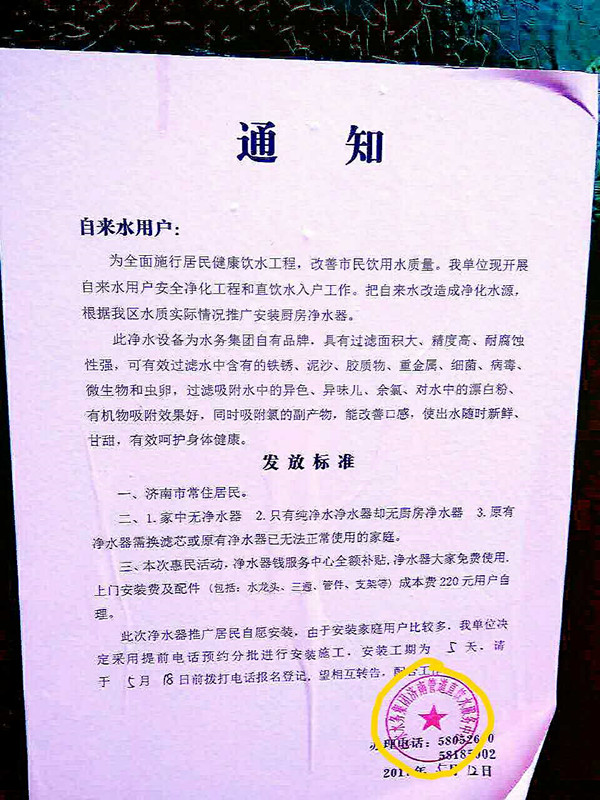北斗辉耀 群星灿烂
——序《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危机》
雷成德
一
捧读张中锋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一个别开生面、新颖别致的研究视角,引人兴趣横生,流连忘返,乐而沉在阅读的享受之中。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大师,世界文坛的顶峰,一百多年来,盛誉不衰,至今仍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拥有亿万粉丝。研究,评论,鉴赏其创作、思想、信仰、社会活动及生平传记的学术专著成千上万,林林葱葱,如茂密的森林,不一而足。这些专著各有其独特的视角,超凡见识,久已为读者所接受。要想从中走出一条新路,实非易事。张中锋钩沉史籍,深读原作,独辟蹊径,脱颖而出,写成这部《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不仅超越了传统规范,而且为托尔斯泰研究献上了新的成果,填补了学界一大空白。
什么是“大地崇拜情结”?张中锋的解释是:“俄罗斯那广袤无垠的土地不但给作家提供着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资源,这里的精神资源不但包括风俗人情、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还应包括人的情感寄托和终极关怀,因而大地崇拜中的‘大地’不再是物质上或物理意义上的‘土地’,而是具有了形而上色彩的理想世界。总的来看,托尔斯泰对大地崇拜的主要内涵是人对自然的原始崇拜。”(见《导言》)。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也说:“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托尔斯泰正是一位从大地获得生命力量的人。张中锋从其对大地的崇拜情结中切入,可谓深得其妙,准确而完美。
托尔斯泰以这一情结始终关照着他的全部生活和创作,宛如一根主线穿透其中,因此牢牢地抓住这根主线,便能清澈透亮地展示托尔斯泰那丰富无比的思想和创作的内蕴,便能鞭辟入里地阐发其思想和创作深度。真可谓北斗辉耀,群星璀璨,美丽而诱人的艺术天空就展现出来。张中锋的这番功力与探究,必然收获至丰至大。
二
本着托尔斯泰大地崇拜情结,辅之以诗意的审美方法,张中锋以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为对象,淋漓尽致地阐发了这一新颖的分析方法,他的选项是正确而合乎时宜的。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震撼世界文坛的史诗,长期以来,学者囿于小说结构宏伟,场面广阔,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等纯文学元素,而并未触及小说中表现出的“大地”情结,其分析评述不免流于表层。张中锋把这些皆置一旁,从托尔斯泰崇拜大地情结切入,开辟了品味与研究这部长篇的新路径。
从“大地”崇拜情结看,《战争与和平》的的确确是一部对生命、生活、青春、激情、幻想与幸福的颂歌。托尔斯泰热情澎湃,对生活现实与前景乐观,因而对人的生命力,尤其是对年轻人生活前景,充满着高度的珍视和深沉的期待,不仅如此,他对社会现实亦持有信心和希望。不论是惨烈悲壮的战场厮杀,还是和平生活的狩猎;不论是宫廷舞会的喧嚣,还是山野庄园婴儿出生的第一声啼哭;不论是年轻人充满欢笑与友谊的聚会,还是窃窃私语的闺蜜亲情,……都给人以生活与生命力蓬勃流动的感人力量,这正是大地赐予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
张中锋在分析《战争与和平》时,首先抓住了小说里显示出的生活真相和人身上蕴蓄的至美品质。长篇小说里浓郁,质朴而厚重的生活气息遮蔽着整个作品,使每个形象、场景、事件和矛盾冲突浸润着爱和昂扬的正能量。这样的作品虽然是由托尔斯泰本人对大地崇拜的情结生发而来的。
长篇小说里不仅有生活的正能量,理性的崇高与乐观,也有生活中的非理性展示。张中锋认为非理性也是一种常见的真实,也是生活本质的有力展示。尽管非理性,人们还不承认其合法性,认为它是一种神秘的事物。张中锋廓清了这些迷雾,公正而合理地承认了非理性的神秘性及其存在。这是一个大胆地发掘,把长期被忽视的艺术表现中非理性呈现出来。例如,《战争与和平》里所写的玛丽在父亲老包尔康斯基濒死床前的纠结心态,十分真实,把目睹老人为病痛折磨的表情,内心渴望老父亲快点死掉,即使老人免受痛苦,又使亲人从沉重的感情压抑下获释,自己即将获得自由的一闪念及其所带来的快感,这似乎是神秘的,不合乎人性之常,绝非理性可支使。但这是绝真的,确实神秘,只有玛丽本人所知。然而她却无法公开说明。非理性常和感情隐私纠缠,只是一时突然冲动,虽不合理,却确实存在。其实在生活中非理性也同样是常见的感情表现。从绝对意义上说,美就是非理性的,人们对自然或其他对象获得美感,并不一定受理性支配。审美活动中并不排斥理性,但也绝不能说,所有的审美活动都是受理性制约的。审美常常是独立的情感活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张中锋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非理性是合理而真切的,这一次勇敢的探索,是十分有益的关于艺术美的突破。
托尔斯泰是位艺术实践经验极其丰富的大作家,也是艺术思维十分活跃的大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首先重视与构建的是艺术画面,直接感受生活事件的感触,引发灵感,从而构思作品情节。由此可见,其艺术思维未必一开始就受理性支配或制约,因而在艺术画面里理性和非理性交叉呈现,相互补充。
从人物造型中,探索非理性神秘性,这是张中锋的一次冒险实践。他敢于提出惊世骇俗的新意,一反传统的纰漏和偏见。这其实是符合艺术实践和艺术规律的,是提高艺术质量,使艺术本质的能量从理性,也许是从抽象干瘪枯燥的概念中解放出来。作为年轻学者,张中锋深悉艺术的本质,提出一系列令人折服的见解。因此,托尔斯泰幻化出的长篇史诗《战争与和平》是大地崇拜情结表现得最为充实,有力和成熟,是托尔斯泰取得至高艺术成就的秘密所在。张中锋的发掘与论述也十分成功。
三
随着托尔斯泰创作的发展与思想的嬗变,他的大地崇拜情结也发生变化,与逐渐形成,并在作品不断表现出的趋向成熟与体系化的托尔斯泰主义相反相成,此消彼长,道德自我完善的道德说教势不可挡地冲击着对大地的崇拜情结,削弱了在作品中的表现力量,这确是托尔斯泰的创作实际。张中锋观察到这种变化,并以《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与评论为契机,划分出托尔斯泰创作前期与中期的巨大分野。
尽管托尔斯泰的道德主义有一个形成过程,远在《童年》中就有萌芽,然而大量涌现并呈强势却是在《战争与和平》及其以后的作品中,直到逝世前夕,紧张而匆忙地编撰成他的绝笔《生活之路》,完全定型。托尔斯泰主义的逐渐强化,削弱,直至损害了他的大地崇拜情结。
出于大地崇拜情结,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尽情地讴歌安娜渴望爱情的诉求,把爱情和生命视为一体。爱情不仅支撑一个人合理的感情生活,而且也是丰富一个人全部生活必不可少的因素。托尔斯泰全力支持和肯定安娜的追求,而且还把她推向社会生活的顶端,成为俯视生活,鉴定生活,预示生活前景的积极力量和崇高权威,使她公开对抗腐朽的上流社会,争取母权和人权。
然而,当安娜站在这个高度,在剧院对抗虚伪残酷的上流社会时,在孩子谢辽沙的生日,勇敢地前去探望,她争取人权和母权的坚决态度却使托尔斯泰震惊。安娜的行为不符合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规范,且突破了它,从此对安娜形象的刻化逐渐涂上了否定的色彩。托尔斯泰渴望的是乐天知命,以忍受,谅解,宽恕对方,然而对生命的爱惜,对爱情的珍视,对生活尊严的维护产生了如此激烈的行为,这是他不愿意期待和看到的。正是从这里,托尔斯泰把列文—吉提的情节线索放大了,以与安娜相对照。
尽管托尔斯泰不喜欢后来的安娜了,谴责她不尽贤妻良母的职责,采取一些庸俗的手法维护爱情等,但作者始终没有把安娜推向放荡女子的行列,仍然坚持维护安娜的自尊与独立的生活态度,只是不愿意再度激烈地对抗社会。然而情节的演变,终于逼她自杀,完成了她悲壮一生的追求。
列文和吉提同样也是追求真挚的爱情,渴望幸福。然而却与安娜的态度完全不同。这两条线索,双水分流,各自独立,平行展开,互不干扰。当时小说发表后,批评家理论家都未认识到两条线索相互关联的基础,认为作品的名称不能概括内容,两条线索相互割裂,很不和谐。莫斯科大学著名教授拉契斯基致信托尔斯泰,指责两条情节线索的断裂,托尔斯泰复信称,他的作品最值得骄傲之处,便是“拱桥的接合处不为人们所发现”(1878年1月27日托尔斯泰给拉契斯基的信《托尔斯泰全集》俄文版,第62卷,第377页)。自此以后,虽无人批评《安娜·卡列尼娜》两条线索的断裂和树立,然多从作品表面情节上找寻二者的接合处,这似乎并不符合托尔斯泰所说的“不为人们所发现”的说法。
张中锋在这方面,遵循托尔斯泰的自述,做了有益而实在的探索,突破和超越了前人的迷误。他合乎逻辑,而又有说服力地解决了《安娜·卡列尼娜》双水并流的结构问题。他用托尔斯泰对大地崇拜情结解决了这个久悬的疑难。安娜热烈追求生活与惨烈的死都是生活本真的写照,而列文所经受的感情苦旅与焦虑也都是时代动荡造成的必然反映。安娜与列文在同时代生活,他们都渴望个人幸福的满足,这是大地为他们提供的契合点。安娜的热情与列文的伤感是同一树枝上的两朵花,有着鲜明的正反典型意义。再说,安娜在第七部自杀,退出了情节,而列文在第八部单独活动,构成单一线索,仿佛为安娜的出路做出回应,可贵的生命不应自戕,这又是大地崇拜情结的鲜明表示。人生的出路不必走上绝路,珍惜生命,呼唤人们认真对待生命,尽管托尔斯泰做出的提示不正确,但生活并不绝望,这仍是对人的珍贵的期待。还有托尔斯泰说的其小说的“接合处不为人们所发现”与张中锋的论点颇相吻合一致。归根结底,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正是大地崇拜情结互相呼应的必然结果。就这一点来说,张中锋对《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做出了超越式的新成绩。
……
托尔斯泰的创作宛如峰峦叠嶂,巍峨挺拔,雄伟庄严,逶迤绵亘的高山峻岭,三大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是其傲视群小的主峰,还有大大小小的中短篇小说、剧作、论著、故事、艺术论文等围绕。张中锋紧紧抓住三大名著辨析论证,其实还用了大量精力,寻求大地崇拜情结在各类作品中碎片化的反映,以便理出一条明朗的线索,见出托尔斯泰大地崇拜情结与道德说教都有发生、发展、形成主线的过程。这既有助于说明三大名著思想与艺术成熟的过程,也勾划出整体思想与艺术的风貌。
当然,有关《复活》评价较低及其其他一些观点还有尚待商榷的地方,但张中锋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毕竟是一部新锐之作,成功之作,破冰之作。在今天学术界的因循之气尚未廓清,外国文学研究仍需要真正启蒙的大好时机,张中锋的实践是有益的尝试。我衷心期待着他新成果的再现。
(作者简介:雷成德:男,1930年生,陕西耀县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为老一代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专家。摘自张中锋著《列夫·托尔斯泰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P.1-13,原序11000字,现删节为45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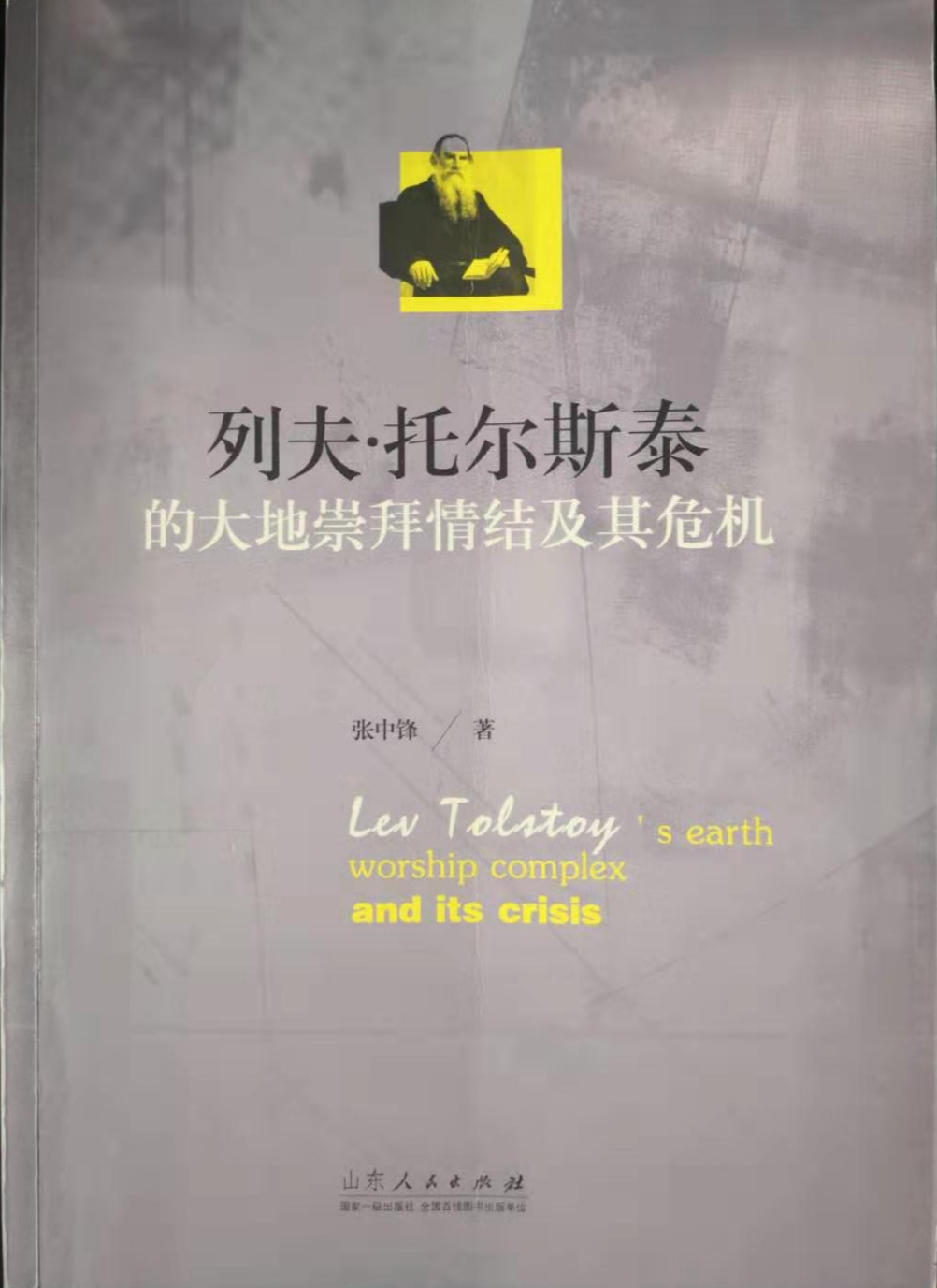
第二章 大地崇拜情结的减弱和崇拜危机的深化
如果说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对大地的崇拜情结还占主导地位,对崇拜中所存着的危机还处在偶然情况的话,那么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则明显看出托尔斯泰对大地的信心已经动摇,信仰危机也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作品中女主人公安娜的自杀和男主人公农业改革的失败,似乎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节 安娜和弗龙斯基人物之间的爱情基础
一
《安娜·卡列尼娜》讲述了两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一对是发生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大都市之间的男女爱情,女主人公叫安娜·卡列尼娜,男主人公叫弗龙斯基;一对发生在莫斯科和乡村农庄之间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叫列文,女主人公叫基蒂,这本来是两个爱情故事,并且表面上看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关系似乎也不太大,若按照欧洲作家的习惯,仅仅安娜和弗龙斯基这一对男女爱情就可以演绎出俄国式的《简·爱》或《包法利夫人》,而无需再把列文和基蒂这对拉扯上。反之,托尔斯泰如果舍弃安娜和弗龙斯基,仅仅把列文和基蒂这一对发生在莫斯科与乡村之间的爱情故事,加以构思布局,也能独立成篇,可是作者非要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大有冒着二者在结构上会出现相割裂的危险,但事实上非但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反倒使人读后有一种珠联璧合,浑然天成之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呢?我们对此所做的解释很多,譬如从主题上讲,安娜的爱情故事这条线索是探讨爱情、婚姻问题的;列文的爱情故事作为另一条线索是在探索农事改革、宗教信仰问题的,二者共同完成了对俄罗斯贵族出路的探讨,再加上人物之间的彼此联系,相互渗透,出现浑然一体的局面是必然的。还有借用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的,其作品结构借鉴了建筑上的“拱形结构”,即《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是恢宏的建筑造型,恰似“凯旋门”,一边是安娜与弗龙斯基,一边是列文与基蒂,而把两个拱柱结合起来的拱顶则是奥布朗斯基一家。应该说这些解释都似乎有道理的,但认真思考起来,还是难尽人意,准确来讲作品结构严谨而完整的效果仍然得益于作者的大地崇拜情结,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实际上作品则包含着内在的联系。虽然作品的标题为“安娜·卡列尼娜”,但“列文”占去的篇幅足够有三分之一强,并且列文先于安娜出现,在安娜死后列文的故事仍然在继续着。不仅如此,安娜的故事发生在大都市,而列文的故事则发生在乡村,列文对大地的崇拜及其危机在间接地“影响”着安娜的爱情和命运。安娜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城市里,但安娜的根基却与大地紧密相连。如果不讲述列文的故事,安娜的故事就很难说得清楚,就像我们不了解土壤的性质就很难判断植物的性质一样。但是如果不讲述安娜,并把它放在“女1号”的位置来讲,我们就不会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作者对大地既崇拜又质疑的矛盾心态,可以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出现仍是继《战争与和平》之后托尔斯泰对大地矛盾心情的延续,即崇拜在减弱,危机在强化,而爱情故事的挫折经历,以及安娜悲剧的产生,则恰恰是作者对大地崇拜情结发生危机的结果。托尔斯泰是一位乡村作家,是一位充满了浓重的农民意识的作家,他只有站在大地上才能看待世界,解释世界,因为西欧科技的发达,早就斩断人与自然的联系,同时也就中止了对作为人的全面主体性的开拓,而托尔斯泰恰恰得力于此,因此,两条线索的联系是内在的,甚至是模糊的,说不清的。对于此,托尔斯泰曾做过这样的解释。
他曾反驳那些认为《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部谈情说爱的沙龙文艺的人们道:“如果近视的研究家认为,我只是想描写我喜欢的东西,如果奥布朗斯基怎样吃饭,卡列尼娜有怎样的肩膀,那他就错了。我所写的一切,几乎一切之中,引导我力求对那些在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想法加以概括……这种联系不是思想上的(我认为),而是由于其它什么东西,但想要用语言直接说明造成这种联系的基础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只能用间接的方式,即通过语言描写形象、行动与事态。”托尔斯泰这段话概括地表明了他一贯的创作原则,即在写作时所注意的从不是什么孤立事件,而是内部互相联系着的种种现象(或思想),以及造成这种联系的根源。
还有托尔斯泰在回复谢·亚·拉钦斯基关于对《安娜·卡列尼娜》中两个主题毫无联系的观点的信中谈道:
您对《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见解,我觉得并不正确。相反,我对我书中的结构极为得意——浑然天成,不露痕迹。这一方面,我下的功夫最多。结构联系不是建立在情节上,也不在人物的相互关系上,这是一种内在的联系。……您看联系找的不是地方,要么就是我们对联系有不同的理解。我所指的联系,正是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东西,这在书里是存在的,您再看一看就会找到。
这种用语言都无法直接说出的一再反复强调的作品“内部互相联系着的种种现象(或思想)”或“内在的联系”,这便是作者对大地崇拜的情结。这种情结的存在才使得安娜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并追求爱情,列文才对土地有着难舍难弃的复杂感情。同时信仰的危机才造成安娜在爱情得到后反到自杀,而列文对土地改革的失败和失望反到皈依了上帝,安娜和列文的结局都似乎作者大地崇拜情结发生危机的表现,而这期间的“联系”才是该作品真正内在的“结构”。
对于这一点也许托尔斯泰同时代的另一个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出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包含了可以为我们欧洲作出回答的事实的规模——我们可以向欧洲指出的那长期寻求的事实。作为一件艺术品,《安娜·卡列尼娜》完美无缺,现代欧洲各国文学中没有类似的作品可以与之比拟;其次,就其思想而言,这已经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的、亲切的东西,亦即在欧洲世界面前显现出我们的特质的东西。如果我们具有如此思维力量和表现力量的文学作品,那么,欧洲为什么拒绝承认我们的独立性,我们自己的文学呢?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地产生的问题。”看来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看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在结构上和依靠大地开拓主体性的独特特性,而这一点正是属于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特性。
因此,纵观《安娜·卡列尼娜》全篇我们不能不说,如果该作中没有列文的故事,安娜的故事就很难说清楚;同样没有安娜的追求及其悲剧结局,也就没法理解列文的苦恼。这种“城市”与“乡村”兼顾的结构,不正反映出作者的矛盾心态吗?
二
按照人物突出的程度,还是先来谈谈安娜吧。
安娜和弗龙斯基虽然生活在大都市,他们之间的结合也和大地崇拜有关,是大地崇拜的间接体现。对大地崇拜也即对生命力的崇拜,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力是大地最为本质的属性。而安娜、弗龙斯基他们之间之所以能够发生爱情,而恰恰在于他们都有着健康的身体、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大自然的最终目的是繁衍,而生命的强盛是保障,这是托尔斯泰对爱情最为朴素的理解,也是符合他的自然崇拜的观念所致。不过对于生命力的赞美就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从而暗合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安娜的爱情追求看作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一时髦解释,其实作为托尔斯泰本人是绝不会想到这一点的,他对资产阶级价值观是深恶痛绝的,他只知道大地的力量就是生命力,一个人只有具有生命力、成为健康的人,才能造就出品性上的真善美禀赋,这一点有点像古希腊人的自然观,看似最为简单的最为朴素的道理,却构成了作者的价值观和创作观。艺术不是哲学,它并不追求思想上的深刻;艺术也不是历史,它并不关心事实本身;艺术也不是科学,亦不追求真实,艺术只服从审美,服从于美的规律。
让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样持有这种观点塑造人物的。先看安娜形象塑造的特点,在车站和弗龙斯基相遇,在弗龙斯基眼中,安娜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夫人的风姿,弗龙斯基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道了一声歉,就走近了车厢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的整个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优美文雅的风度,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表情带有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好像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弗龙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弯曲了的隐隐约约的微笑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整个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这里所说的“过剩的生命力”,也就是旺盛的生命力,这即是安娜之所以具有诚实、真诚品质的“物质”基础,也是其之所以不安于现状,要追求“个性解放”的原因,这两点在基蒂眼中的安娜就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安娜的漂亮首先在于生命力的旺盛。在基蒂眼中,“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贵妇人,也不像有了八岁孩子的母亲。如果不是眼神里有一种使基蒂惊异而又倾倒的、非常严肃、有时甚至非常忧愁的神情,凭着她的举动的灵活,精神的饱满,以及她脸上那种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眸里流露出来的蓬勃的生气,她看上去很像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郎。基蒂感觉到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但她心中却存在着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境界,那境界是基蒂所望尘莫及的。”作为少妇的安娜仍然青春勃发,特别是“诗意”的境界,也即自由的境界,自由意志的张扬,这恰恰是生命力得以张扬的境界。当初基蒂邀请安娜参加她的订婚舞会时嘱咐安娜要穿淡紫色服装,以适合她的年龄和身份(也可能暗含着避免“斗妍”的小心眼——论者注),但是安娜却有自己的打算。基蒂发现,“安娜并不是穿的淡紫色衣服,如基蒂希望的,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衣裳,她那看上去好像老象牙雕成的胸部和肩膊,和那长着细嫩小手的圆圆的肩膀全露在外面。衣裳上镶着威尼斯的花边。……基蒂每天看见安娜;她爱慕她,而且常想象她穿淡紫色衣服的模样,但是现在看她穿着黑色衣裳,她才感觉到她从前并没有看出她的全部魅力。她现在完全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现在她才了解到安娜可以不穿淡紫色衣服,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人总是盖过服装,她的衣服在她身上决不会引人注目。她那镶着华丽花边的黑色衣服在她身上并不醒目;这不过是一个框架罢了,令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同时基蒂也看到了安娜的另一面,“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基蒂的眼光引到安娜的脸上。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色衣裳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脖项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鬈发是迷人的,但是在她的迷人之中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是的,她身上有些异样的、恶魔般的、迷人的地方。”这种“可怕和残酷的东西”,以及“异样的、恶魔般的、迷人的地方”,则恰恰是安娜性格的另一面,这便是“恶”的一面,应该说基蒂的眼光是很有见地的,这正是安娜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女性特点之个性所在。生命力的旺盛与张扬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显示出了生命要发展要自由从而趋向善的特性,另一方面因为这种生命力的张扬必然要突破世间的道德规范,因此,生命力面对这些世俗道德而言,则呈现出恶的一面,还有,生命力的张扬也伴随着欲望的张扬,生命是美好的,而欲望则带有动物的性质,因而在呈现善的一面的同时,也呈现出恶的一面。生命力的蓬蓬勃勃体现着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精神,而欲望恶,则表现出其对世俗道德加以超越所带来的快感,另一方面也带来对大地诗意本身解构所带来的忧虑。托尔斯泰身上复杂的矛盾在安娜身上体现为丰富的个性,而这个个性却形成了安娜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着弗龙斯基离开了基蒂。应该说基蒂也是很美的,在列文的眼中基蒂是那么的美,“他想到她的时候,他心里可以生动地描绘出她的全幅姿影,特别是她那么轻巧地安放在他那端正的少女的肩上,脸上充满了孩子样的明朗和善良神情的、小小的一头金发的头的魅力。她的孩子气的表情,加上她身材的纤美,构成了她的特别魅力,那魅力他完全领会到了;但是一向使她意外惊倒的,是她那双眼睛温柔、静穆和诚实的眼神,特别是她的微笑,总是把列文带进仙境中,使他流连其中眷恋难舍,情深意切,就像他记得在童年一些日子里所感觉的一样。”不可否认这里有恋爱中人的诗意想象。基蒂倒底有多美呢,我们可以在弗龙斯基准备向她求婚的舞会上,看作者刻画的基蒂形象。
这是基蒂最幸福的日子。她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她的花边披肩没有一点下垂,她的玫瑰花结也没有被揉皱或扯掉;她的淡红色高跟鞋并不夹脚,而只使她愉快。金色的假髻密密层层地覆在她的小小的头上,宛如是她自己的头发一样。她的长手套上的三颗纽扣统统地扣上了,一个都没有松开,那长手套裹住了她的手,却没有改变轮廓。她的圆形领饰的黑天鹅绒带特别柔软地缠绕着她的颈项。那天鹅绒带是美丽的;在家里,对镜照着她的脖颈的时候,基蒂感觉到那天鹅绒简直是栩栩如生的。在这舞厅里,当基蒂又在镜子里看到它的时候,她微笑起来了。她的赤裸的肩膊和手臂给予了基蒂一种冷澈的大理石的感觉,一种她特别喜欢的感觉。她的眼睛闪耀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不禁微笑了。当她还没有跨进舞厅,走进那群满身是网纱、丝带、花边和花朵,等待别人来请求伴舞的妇人——基蒂从来不属于那群人——的时候,就有人来请求和她跳华尔兹舞,而且是一个最好的舞伴,跳舞界的泰斗,有名的舞蹈指导,标致魁梧的已婚男子,叶戈鲁什卡·科尔孙斯基。
这里充分表现了基蒂的美和求婚前的喜悦心情,以及虚荣心即将得到满足的兴奋。应该说基蒂也是很美的,美到无可挑剔,并且基蒂身为姑娘,年龄身份均占优势,为什么弗龙斯基会与之解除“婚约”投向安娜呢?因为基蒂的美是大自然赋予她那个年龄阶段所具有的美,基蒂不过是当时都市中的一个时髦标致的女孩而已,她身上所洋溢出来的生命力显然不如安娜,同时也更缺乏安娜的“诗意的美”。安娜的美是富有个性的,是超尘拔俗的,基蒂追求爱情实则是追求婚姻,而安娜追求爱情则是追求自由。基蒂的背后只有青春、时髦和符合时宜的婚姻标准;而安娜背后有的是大地情怀,是生命里的张扬。安娜的美充满了野性,它是现代的、有力的,而基蒂的美则是古典的,它是和谐的,但也是纤弱的,缺乏个性的。安娜原本是一个来自乡村贵族的不谙世故的单纯女孩,经姑妈安排,嫁给了年龄上长她18岁的大官僚卡列宁。不幸的婚姻使得自然情感被压抑了八年,但并没有消失,反倒愈压愈烈,只要机会到来,随时都可以爆发,而今终于遇到了时机,遇到了突破口,这就是年轻的军官弗龙斯基。
另外还要看到安娜发生恋爱的地方是莫斯科,尽管在彼得堡过了八年无爱的婚姻生活。莫斯科真的和彼得堡不一样呵,彼得堡是一个欧洲式的大都市,它早已和大地斩断了联系,失去了诗意和激情,人们管彼得堡人为生活在俄国的欧洲人。而莫斯科则始终被看作是纯粹俄罗斯的,是属于东方的,是俄国的一个大庄园而已,它也就更靠近大地。当安娜只身初次来到这个古老的温情脉脉的城市,她就再也难以抑制住长期被压抑的情感。
三
弗龙斯基之所以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安娜的美,这也说明弗龙斯基也不是很简单的人物,因为弗龙斯基将为此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还要残忍地伤害一个年轻姑娘的心。那么弗龙斯基是怎样的人呢?作者通过的列文的眼睛向我们展示出来。“弗龙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黑发男子,不十分高,生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决的面孔。他的整个容貌和风姿,从他剪短的黑发和新剃的下颚一直到他宽舒的、崭新的军服,都是又朴素又雅致的。”这里的“身体健壮”也表明了弗龙斯基生命力的旺盛,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一下子就爱上安娜,并不顾一切地追求他的原因。不管我们怎么说,弗龙斯基对安娜是热情的、诚恳的、忠诚的,因为旺盛的生命力也使得弗龙斯基产生了主动追求真善美的冲动,看来没有生命就没有真善美,就没有爱,这就是托尔斯泰的逻辑,也是其创作的特点所在。当然弗龙斯基的生命力与安娜相比,还是弱小一些,这也就为什么弗龙斯基仅仅是作为安娜的“陪衬”角色的原因了。
与生命力旺盛的安娜和弗龙斯基相比,卡列宁的生命力则是衰朽的、枯萎的。卡列宁身材瘦小、枯干、谢顶,说话尖声细气,长着两个扇风耳朵,习惯于把手指扳得咔咔响,难怪安娜一见到卡列宁做出这样习惯性动作时,就会产生生理上的厌恶。卡列宁这样衰弱的身体,是反自然的,依照托尔斯泰的逻辑,就只能产生假恶丑的生命体,事实上卡列宁也是非常虚伪的和缺乏感情的,不管怎么样,在自然的审判台上卡列宁已经站在被告席上了,因为他和安娜的婚姻是违背自然的,也即违反人性的,请看安娜是怎样对卡列宁所进行控诉的。“他们说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虔诚、道德高尚、正直、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一切我都会忍受,一切我都会饶恕的:但是不,他……” “他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在这样的状况下,安娜的追求就有了合乎道德的动机,当然这里的道德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大道德,而并非世俗的道德,安娜身上之所以会出现“被压抑的情感”、“诗性的”、“残酷的”等精神面貌,在这种婚姻环境中,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二节 安娜与弗龙斯基的感情危机
对生命力的赞美固然是张扬主体性和实现个性解放的有效手段(当然作者不一定能上升到如此的理性高度),但是这种对生命力的张扬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弊端。张扬生命固然存在追求自由的精神维度(诗性的自然),但也不可否认生命本身就包含着自然欲望,也是人作为生命存在最为根本的。欲望属于物质性的东西,欲望释放的背后便存在着虚无维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约会更多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而缺乏像《简·爱》中简与罗切斯特之间那样的精神交流。事实证明最后俩人同居后竟都陷入空虚寂寞的境地,为了排除寂寞弗龙斯基不得不再次进入起先为了爱情而被他所鄙视的社交界,安娜则只能仅仅抓住弗龙斯基,因为社交界已经对她关上了大门,她无法排遣寂寞,弗龙斯基成了他唯一的稻草,在这样的状况下安娜悲剧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尽管托尔斯泰责怪二者或虚荣心作祟,或沦为情欲的奴隶而没有达到更高的追求,试想生命力本身不也是欲望吗?生命的存在状态不就是欲望的不断张扬吗?这种悖论恰恰是托尔斯泰自身理论的缺陷所造成的,是大地崇拜本身的结果。还有,生命力张扬的实质不过是自然生命的繁衍,而生命繁衍的形式就是注重家庭的组合,而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爱情恰恰是反家庭的。安娜在和弗龙斯基相爱的最初那一刻就拒绝嫁给弗龙斯基,因为安娜生命力的张扬不是物质的、繁衍的,而是诗性的、自由的。从表面上看安娜之所以不能嫁给弗龙斯基是因为她太爱孩子,以及丈夫卡列宁的阻挠,实际上安娜对于再婚的后果是早已有所察觉的,尽管弗龙斯基非常执意结婚。弗龙斯基的生命力不及安娜而使他难以察觉其埋在内心更深处的忧虑,他回归社交界满足功利心的再起,也说明弗龙斯基爱情追求的精神境界要低于安娜。不要说结婚,仅仅同居就已经验证安娜所预想的一切,那么进亦忧,退亦忧,安娜的未来选择就只能是自杀了。
当安娜与弗龙斯基相爱时其生命力达到极点时,极点也即终点,此时的托尔斯泰就已经为安娜的自杀结局做了“准备”,让他们到欧洲去旅游,从而让他们“沾染”上欧洲文明的缺陷——极端个人主义(这便制造了一个杀人借口),于是生命力的张扬就变成了欲望的放纵,安娜就由娜塔莎变成了海伦。当然尤为关键的是在作者看来此时的安娜和弗龙斯基都脱离了大地,脱离了“地气”,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之人,尽管他们回国后一直住在弗龙斯基的农村庄园,但这里的庄园并不对耕种稼穑感兴趣,也和大地无关。弗龙斯基的庄园带有英国味道,已经不是俄罗斯的了。作品中作者极力描写安娜和弗龙斯基同居的庄园之豪华,因为弗龙斯基农庄并不注重农业的收种,而是注重粮食加工,注重饲养马匹,修建乡村医院等,这样的庄园不是农业经营,而更像是一个现代企业。这与列文所经营的以种粮食为主的庄园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列文经营得有些惨淡,甚至濒临破产,但在托尔斯泰看来列文却没有失去土地,大地崇拜情结虽存危机,但精神之源仍在;尽管弗龙斯基的庄园效益很好,但是作者却认为弗龙斯基的行为已经远离了大地,他们虽身体依然强壮,但因离开大地而会导致精神不断枯竭,最终强壮的身体渐渐变成了欲望的身体。
实事求是地来讲,安娜住在弗龙斯基家衣食无忧,弗龙斯基对安娜感情忠诚,他们还有自己的小女孩(爱情的结晶),即使不能结婚而这样一直同居下去也是无所谓的。安娜的优越处境,曾经让来拜访的多莉羡慕不已。“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见那辆她从未见识过的雅致的马车,那一匹匹出色的骏马和环绕着她的那一群优雅而华丽的人,弄得眼花缭乱了。然而最使她感到惊讶不置的还是在她所熟悉而钟爱的安娜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换上另外一个女人,一个眼光不那么敏锐、以前不认识安娜、特别是一个没有起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路上起过的那种念头的女人,在安娜身上是看不出什么异样的地方的。但是现在多莉被那种仅仅在恋爱期间女人身上才有的。现在她在安娜脸上所看出的那种瞬息即逝的美貌所打动了。她脸上的一切:她脸颊和下颚上的鲜明的酒靥,她嘴唇的曲线,她面孔上依稀荡漾的笑意,她眼里的光辉,她的动作的优雅与灵活,她的声音的圆润,甚至她用来回答韦斯洛夫斯基的那种半恼半笑的姿态,——他请求许他骑她的马,好教它跑时用右脚起步——这一切都特别使人神魂颠倒;好像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高兴。”婚姻只是外表上光鲜,多莉的羡慕并不了解此时安娜内心的烦恼,也由此看来多莉的平庸。
尽管在她人眼里安娜生活条件如此优越,可是在作者观念的支配下他的性情却变得越来越难以理喻了,经常地发着无名的火,吃着无名的醋,真的有点患了歇斯底里症了。长期的感情折磨使得弗龙斯基更多地把安娜这种爱当成了负担和累赘。安娜为莫名的焦虑所控制,空虚、孤独,甚至负罪感在折磨着她,这大概与失去大地之源有关。我们看一下自杀之前的安娜的思绪,“‘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的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她继续想下去。‘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是他却越来越想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地疏远起来;这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他不爱我,却由于责任感而对我曲意温存,但却没有我所渴望的情感,这比怨恨还要坏千百倍呢!这简直是地狱!事实就是如此。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旦结束,仇恨就开始了。’”为什么要求对方献身于自己呢?这不是极端自私吗?何况献身到什么程度?这是连安娜自己也难以说清的。生命是健康的、向上的,欲望是物质的、消极的,失去大地联系的安娜变得偏执与自私,如何回归大地?当然自杀是悲剧的,可这确实是安娜最好的选择,当安娜血染大地之时不恰恰是一种为大地献祭的行为吗?这种行为作为个体是悲惨的,但作为奔流不息的生命来说,这却是安娜最后的诗性表达。“不自由,毋宁死。”因此,安娜的价值也仅仅是生命力的短暂释放,这种悲剧性的释放便带有了尼采色彩。
(选自张中锋著《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危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章的第一、二节,P.99-110,10000字。)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王封

闂備礁鎲¢〃鍡楊熆濡皷鍋撻惂鍛婂12闁诲骸鍘滈崑鎾趁归敐鍡樺仩闁稿绻堥幃妤€鈽夐幒鎾寸彆濠电偛鎳岄崐婵嗙暦椤栫偛骞㈡慨姗嗗幖濞戯拷162 婵犳鍣紞鍥箯閿燂拷

婵犵數鍋炲ḿ娆愵殽缁嬭法鏆﹂柍鈺佸暟闂勫嫰鏌涢幇顖氱毢闁硅棄绉归弻娑滎檪闁瑰嚖鎷�30缂傚倷绶¢崑澶娾枍閺囩姵宕插ù锝呮贡椤╂煡鏌ㄩ悤鍌涘 闂備浇鐨崘銊х◤濠殿喚娅㈤幏锟�

闂傚倷鐒﹁ぐ鍐矓鐎垫瓕濮抽柨鐔哄Т閻愬﹥绻涢幋鐐ㄧ細闁诲繑濞婇幃妤€鈽夐幒鎾寸彅闂佺儵鍓濋悷褔骞忛悩娲绘晬婵炲棙鍨归幉顏呬繆閵堝懎鈧綊鏁冮姀銈呯劦妞ゆ帒锕ョ€氾拷

闂傚倷鐒﹁ぐ鍐矓鐎垫瓕濮抽柨鐔哄Т鐎氬鏌涘┑鍡楊仾缂併劍宀稿娲敆婢跺﹤绠哄┑鈽嗗亖閸婃牜绮嬪澶嬪€绘俊顖濆吹閻ㄨ螖閻橀潧浠滅€殿喛鍩栫粩鐔兼晸閿燂拷

闂傚倷绶¢崰妤呭垂閻㈢數鐜婚柣鎰嚟闂勫嫰鏌涢幇顒傛勾濞存粣缍侀幃妤€鈽夐崘宸喘闂佽桨鐒﹂幑鍥嵁瀹ュ鏁婇柛蹇擃槸娴滅偓绻濇繛鎯т壕缂備焦妫冮弨杈╃矉閹烘垟鏋庨煫鍥ь儏娴犮垽姊洪悙钘夊姷闁瑰嚖鎷�

闂備胶鎳撻悺銊╁垂闂堟耽鐟拔旈崨顓犵厬闂佺懓鐡ㄧ换鍕敂閹绢喗鐓曢柕澶涘閳笺儵姊洪崣澶岀煉鐎殿噮鍓熷鍫曞垂椤旇偐鐟茬紓鍌欐祰娴滎剚鎱ㄩ幎鑺ュ殘闁硅揪绠戝Λ姗€鏌涢妷鎴濆閳ь剨鎷�

闂備礁缍婇弲鎻捗归崶顒€纾婚柛灞剧矋閸嬫﹢鎮橀悙闈涗壕缂傚秮鍋撻梺鑽ゅТ濞诧箑煤濠婂牆纾婚柨婵嗩槸缁犮儵鏌嶉崫鍕仼婵炲牓绠栭弻娑滅疀鐎n亜顬堝┑鐐舵彧閹凤拷

闂備胶绮〃澶愶綖婢跺⿵鑰块柡鍥ュ灩閻ょ偓銇勯弮鍌滄憘闁告柡鍋撻梻浣稿悑濠㈡﹢宕崘宸€剁紓浣股戝▍鐘绘煟閹邦厼绲荤€垫澘绉瑰濠氬礃閵娧傝檸闂佷紮闄勭划灞炬櫏闂佽法鍣﹂幏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