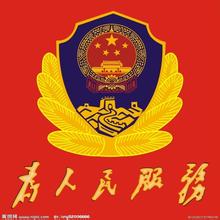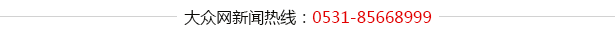1938年5月16日,美国《生活》杂志刊登的一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资料来自《南京大屠杀真相》)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关于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杀人比赛”的报道。

1938年美国《瞭望》杂志刊发日军用中国俘虏进行刺杀训练的照片。

意大利《晚邮报》1937年12月11日关于“南京沦陷”的报道。

1937年12月28日,上海报纸转载《伦敦时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哈罗德·约翰·田伯烈。他根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文书、通讯及个人日记、信函于1938年3月在上海编成《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in China》一书,并同时在纽约、伦敦出版英文版,在中国出版中文版。

《世界画报》于1938年2月2日刊登嘲讽日军侵华的漫画。
■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特稿③
斯提尔是第一个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记者。他用“地狱中的四天”来形容日军攻占南京后的经历。“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今天经此城门过,发现要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1937年12月1日,日军华中方面军下达攻占南京的作战命令。因遭日机接连数月无差别轰炸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南京城,岌岌可危。
中国媒体在南京沦陷前已经全部奉命撤退,西方记者因为当时特殊的中立者身份,得以留在南京城中,以“第三者”的视角真实地报道了日军南京屠城的种种难以形诸笔墨的悲情惨景。
逆着逃难人流前进
当南京陷入危情中时,34岁的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契包德·斯提尔正奔波在从济南到南京的旅途中。他在12月2日从南京发往《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报道中感慨:“在中国的铁路线上,战争的影响以一种最恶劣的方式得以表现。伤员、贫民以及逃难的富人,所有的人都在躲避日军的炮火而涌向列车。”
在济南,当他正准备乘上预定的列车时,难民们蜂拥而至。已经习惯在拥挤、推搡的人群中奋勇前进的斯提尔,这次还是输给了难民。“丢盔弃甲的我最后不得不退了下来。当几小时后下一班列车到来时,我终于冲在前面,在有顶货车里抢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当然,这辆货车也在转眼间就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富人和穷人,以及他们的财产。”
然而,在拥挤不堪的状态下到达徐州后,情况完全发生了改变。换乘开往南京的列车,斯提尔发现,列车几乎是空的,“因为没有人想去已经注定要完蛋的南京。我是豪华的一等卧铺车厢中唯一付了车费的乘客。这辆车原本用于将南京的官僚们运往汉口,但现在却开往首都,去装运新的货物。”
抵达南京对岸的浦口,令斯提尔应接不暇的依旧是成千上万等待搭乘火车的人们和堆积成山的货物。从江岸到南京北门再到市中心约3英里的路上,他一直逆着川流不息的逃难人流前进。虽然关于多少人离开了南京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斯提尔认为,留下的大概最多只有南京1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
到达南京后,斯提尔了解了南京的战事:“虽然南京面临着孤立、覆灭的现实危险,但政府领导者似乎已决定了要死守南京。大多数军队已经撤离,然而为了要让日军在占领首都时付出最大的牺牲,必要的守军还是留了下来,一些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构筑城门的防守工程。”
与慌乱无助、急于逃难的南京老百姓相比,有机会撤离的美国人显得要镇定得多。斯提尔12月7日发往《太阳报》的专电中表示,住在首都的29名美国人之中,仅有8人听从了撤离的警告,并有至少14名美国人打算在南京被包围期也一直留在城内,除非发生万不得已的情况。“这些留守者大多数是传教士。在决定留下时,他们没有表露出丝毫的英雄气概,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义务。他们说,必须留下来守护教会的财产,给予中国同僚们信心,帮助现在仍在计划中的安全区——这关系到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
观察战事遇险情
日军一步步逼近,针对外国人的撤离警告一遍又一遍,出于职业道德,斯提尔还是决定留在南京。与他一起留守下来的还有他的四位同行:美联社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德丁、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阿瑟·门肯以及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
相对于留守安全区的护卫者传教士来说,为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而四处奔走的西方记者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出生于苏州的麦克丹尼尔,取得北卡罗来纳大学硕士学位后,1935年成为美联社的记者。由于敌我双方的战事报道相互矛盾,12月5日,他开车到南京城以东地区采访战事的发展。不巧,一发炮弹在车前方200码处爆炸,并将他的车子掀了起来。这次遇险经历并没有令麦克丹尼尔畏惧,反而令他欣喜,他不仅寻获了战争的进程,而且发现了离南京城28英里远的日军防线。
12月7日,麦克丹尼尔又一次到南京城郊观察战事。他开车15英里,穿越被撤退的中国军队放火烧掉的村庄。驶经汤山温泉时,麦克丹尼尔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无人的区域,双方的炮弹在头顶上呼啸。他迅速把车倒出来,这才发现,当时离日军炮兵阵地只有300码远。
喜欢近距离观察前线战斗的德丁,不仅在采访中直接遭遇了战斗,还曾徒步走过地雷桥。他在12月7日发给《纽约时报》的特电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经历:
“战战兢兢地步行过了桥,来到了那座士兵指过的山丘脚下的村庄里。从左侧断断续续传来炮轰声,越往前行,机关枪哒哒哒连发的声音就越大。”
“绕过山脚,我们来到一个可以将战线一览无遗的地方。在前方一英里远的地方,中国和日本的军队隔着狭窄的山谷正在进行激烈的枪战。在左侧,双方的炮兵队越过三角形的山顶进行交火,在右侧遥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听见日军大炮正在炮轰汤山附近阵地的中国军队。”
斯提尔则记录了日军围攻南京战争的恐怖,他在12月10日发往《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报道中说:“今天我在一个易于眺望的地方观察到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在南京的中央以及南部地区,继而纷纷爆炸,平均一分钟四回这样的频率。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浓重的烟雾,很难判断战况。”
“日本的炮击飞机又来了,在距离美国大使馆仅有600码的小山上丢下炸弹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剧烈地摇动了起来。在那个小山上,中国军队的一门高射炮对着每一架飞来的飞机进行猛烈地攻击,但是光是打出炮弹,却没有效果。”
当南京最艰难的时刻即将来临之时,斯提尔也感受到恐惧来袭的滋味。“夜幕低垂时,充满持续不断的轰炸、机枪扫射的一天终于降下了帷幕。一天的轰炸、扫射,将数以百计血肉模糊、肢体破碎的人送进医院,其他残缺不全、失去生命的躯体奇形怪状地散落在弹坑四周。”
“晚上,几次雷霆般的爆炸向我们揭示了明天双方开始炮战时将会出现的情况,那将比轰炸更加难以捉摸,惊心动魄。”
和被围困在城墙内的人一样,希望能尽快没有痛苦地度过这艰难时刻的斯提尔,难以如愿。
疯狂的南京景象
12月13日,令人心惊胆寒的轰炸声终于停息。南京城的艰难时刻没有远去,而是进入到更加恐怖的时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让亲眼目睹一幕幕惨状的西方记者震惊、愤怒。
斯提尔是第一个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记者。1937年12月15日,他经由“瓦胡”号军舰发出的特讯刊登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头版。
文章中,他用“地狱中的四天”来形容日军攻占南京后的经历。“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也许在5000-20000人之间。由于陆路已切断,中国军人通过挹江门涌向江边,挹江门迅速堵塞。今天经此城门过,发现要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
“日军闯入外国人的房屋,其中包括美国大使尼尔松·约翰逊的府邸。劫掠过后,看上去犹如星期日教会学校的野餐,一片狼藉。”
“在美国人开办的金陵大学医院,他们抢去手表、钱财。至少偷走两辆美国人的汽车,撕掉美国国旗。他们甚至闯进难民营,许多穷人仅有的几个铜板亦遭洗劫。”
12月15日当天,斯提尔及其他日军攻城开始后第一批离开首都的外国人登上“瓦胡”号军舰。离开南京之际,他们见到的场面是“一群300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斯提尔将其称之为“近几天疯狂的南京景象最典型的写照”。
门肯和德丁两位美国记者也与斯提尔一起登舰。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门肯游历极广,曾开车穿越阿拉伯沙漠,去南美探险,还曾采访过西班牙内战。在南京,他拍摄了日军攻陷南京城的情景。离开南京后,他在12月17日刊登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文稿中揭露,“中国男子只要被发现有在军队服役的痕迹,即被押到一起,遭处决。”
德丁撰写的大篇幅报道则刊登在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他也记录下自己的所闻所见:“屠杀平民的暴行普遍存在。周三,走遍全城的外国人发现每一条大街上都有死难的平民。他们中间有老人,有妇女,还有儿童。”
“警察和消防队员成了日军专门袭击的目标。很多人都是被刺刀捅死的,从伤口处可以看出,有的死者是被极其野蛮、极端残忍地杀害的。”
“许多中国人向外国人报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劫走,遭强奸。他们乞求帮助,但外国人通常对此爱莫能助。”
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也是12月15日乘坐英舰“瓢虫”号离开南京的。在12月13日激烈的南京保卫战结束后,史密斯曾判断,“随着日本人的出现,中国的平民百姓似乎有一丝轻松的感觉。”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观点。12月17日,史密斯抵达上海后,于第二天向伦敦的《泰晤士报》发出一篇报道,指出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了有组织的大屠杀,暴行甚至波及了南京安全区。
无力救人的“中立者”
最后一个离开南京的西方记者,是麦克丹尼尔。12月16日,他乘坐日本舰“津贺”号由南京去上海。12月18日,他所写的战争日记得以刊登于《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他在南京那些危险、动荡不定的日子也为读者所知。
“12月13日,在城北面的城墙附近,突然看到日军从城墙的缺口爬上来。日本兵举着枪向我冲来时,我举双手,从车子出来。”经日军同意,他爬过残破的城门,穿行在堆满中国军人尸体的街上。路上到处是日军的恶作剧——“被砍下的头颅平放在路障上,嘴里放了块饼干,另一个嘴里插了支长长的中国烟斗。”
回程的路上,麦克丹尼尔边走边协助留守南京的外国人帮中国军人解除武装,四处转悠着把机枪、手榴弹、手枪装进汽车,催促士兵脱掉军装,以免被日军处死。
12月14日,麦克丹尼尔目睹日军洗劫全城。他看见一个日本兵在安全区用刺刀威逼老百姓,共勒索了3000块钱。“沿着横陈着人、马尸体的街道走到北门,见到第一辆日本车子驶进城门,车轮在碾碎的尸体上打滑。”
12月15日,麦克丹尼尔陪同大使馆的一位仆役去看她的母亲,在沟里发现了她的尸体。下午,看见几位协助他解除武装的士兵被拉出去枪毙。夜里,又看到500名老百姓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手被捆绑着,由手持中国大刀的日本兵从安全区押出去。没有人活着回来。
发现使馆里的工作人员已孤立无援,没有水,也不敢步出门外,麦克丹尼尔花了一个小时,到街上的井里打了几桶水拎回使馆去。
12月16日,麦克丹尼尔启程去上海之前,日本领事馆拿来“不得入内”的告示,贴在使馆的房屋上。“去江边的路上,见到街上的尸体又多了许多。路上遇到一长列中国人,手都被捆绑着。一个人跑出来,到我跟前双膝跪下,求我救他一命。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最后的记忆是: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
无法推翻的大屠杀铁证
西方记者撤离南京之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却并没有由此中断。他们与美国《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阿本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等南京大屠杀期间不在南京的新闻媒体人一起,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对这一事件保持关注。而美国《时代周刊》《读者文摘》、英国《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卫报》、西班牙《洪水报》、意大利《晚邮报》也利用在南京的外国人士的日记和书信,编写相关报道,使外界有机会了解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洪水报》1937年12月13日引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消息,报道了两名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百人斩竞赛的残忍行径。并用“清洗”一词来描述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的大屠杀行为。
《时代周刊》1938年4月18日报道的《竹筐惨案》事件,是从美国传教士威尔逊医生那里得知的。“典型而令人惊骇的一桩惨案主人公是1月26日被人用竹筐抬到南京教会医院的一位年轻中国姑娘。她说丈夫是名警察,日军将她从安全区的一间棚屋劫持到城南的同一天,她的丈夫被日军行刑队抓走,在城南,她被关了38天,每天被日军强奸5至10次。经教会医院检查,她已感染上3种最常见的性病,最终由于阴道溃烂对日军失去使用价值。”
《视野》杂志1938年6月2日报道称:“腐烂膨胀的尸体随处可见,在街上,在屋子里,填满城内每座池塘,高高地堆积在城外江边,野狗穿行于尸骨之间,恶臭难闻到极点,躲都没法躲,穿的衣服里都渗透了臭味。……几十名身穿规定制服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亦遭屠杀。他们的身躯倒在他们刚才搬运的尸体之上。”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张宪文教授接受采访时介绍,随着死亡数字的不断上升,美国媒体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来描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时,美国记者很注意强调一个事实:即日本当局当年实际上对南京大屠杀是知情的,但他们总辩解说大屠杀是在上海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反而说明日本对其军队失去了控制,日本是一个“污点”国家。
揭露日本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掩盖,也是美国媒体关心的事,《视野》杂志1938年6月报道说:“在大规模集体屠杀毫无间歇地进行之际,日军飞机在空中撒下传单:‘所有回到家园的善良中国人,你们的朋友日本皇军都会供吃、给穿。’‘对于那些没有被蒋介石军队的恶魔愚弄的中国人,日本希望成为良善的邻邦。’传单上用彩色画了位英俊的日本兵,像基督般抱着一个中国孩子在他怀里。在他脚下,一位中国母亲拜谢他赐予的几袋米。……圣诞节后第三天,一艘日本商船由上海驶抵南京,船上挤满了日本的观光客,他们中有许多妇女,穿着鲜艳的和服,五颜六色的腰带在焦黑的废墟中显出极为怪异的不协调。她们被小心翼翼地领到已清理掉恶臭尸体的几条街道。她们亲切礼貌地给中国孩子发糖,轻轻地拍拍他们惊恐异常的脑壳。”
此外,中国媒体虽已撤离,但他们一方面收集了不少逃出南京的目击者记述,一方面从外国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中汇集了不少资料,国共两党的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报道。
“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的西方新闻记者,亲历古城南京这场浩劫,目睹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后,以其良知真实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详尽地记录下南京人民那段苦难历程,勇敢地向世界发出来自死城南京的呼声。”张宪文表示,作为“第三者”的亲历史料,这些新闻报道与在国际安全区实施救助工作外国传教士、教师的日记、书信及各种文字材料一样,非常珍贵,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大屠杀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