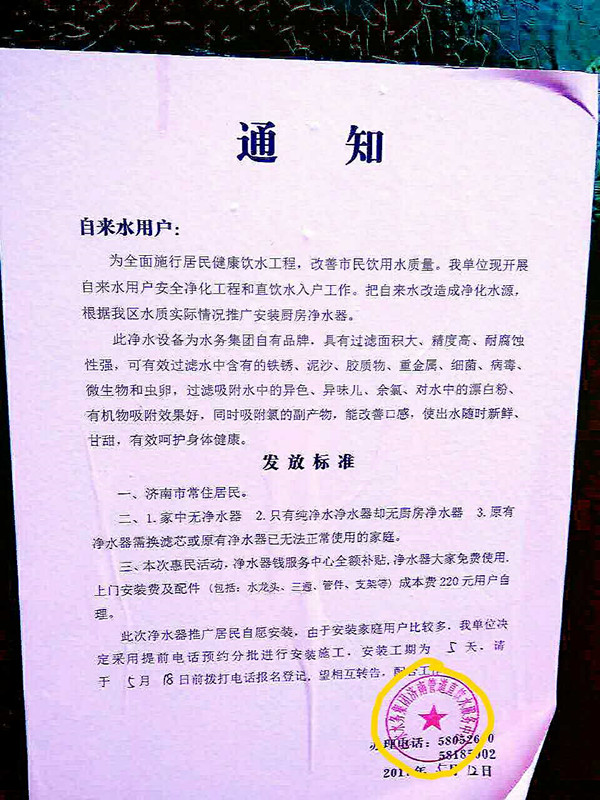从2007年开始,就有媒体陆续报道前中科大校长朱清时将会领衔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时隔三年之后,南方科大终于在9月30日开始动工建设校园,似乎正式开启了这所被赋予太多“改革”意义的新大学建设的帷幕。
不过根据媒体的相关报道,筹建过程似乎也并不如朱清时预想的那样顺遂,比如在购买设备、招生方面所遭遇到的各种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也让这位豪情万丈的新校长初尝“特区”行政官僚化方面的“不特”之处。
不过这些小磕小绊并没有浇灭朱清时开辟高校教育改革新纪元的梦想,他仍然坚持认为,目前是打破教育体制行政化的最好时机,他说,“在一个行政化体制普遍存在的国家,要把现已行政化的教育逐步改变成学术主导的教育。是非常艰难的,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想,如果这件事用30年的时间能够做成,那会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对于今天社会里的每一种理想,我们本应给予足够的理解与尊重,但是理想的达成却无法脱离现实,既然朱校长以30年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期限,他必然会认为现在已经显现出某种改革的契机,比如深圳市政府对他的各种优惠条件乃至特权,还有他作为前中国科大校长所积累的教育界的各路人脉资源。不过,上述种种其实都无法疏通今日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通道,那就是高校与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朱校长认为“政教”之间最大的矛盾是高校行政化,初看似乎有其道理,毕竟只要身处高校,就会感受到教授地位之低下与行政官僚之“颐指气使”,教授没有权力,自然谈不上从教育的角度去治理学校,而官僚管理行政事务,根本目标要么是效率,要么是维稳,让官僚来统管教育,显然会在很多方面背离教育的一些基本逻辑,比如教育讲的是“百年树人”,官僚要么想的是“死水微澜”,要么就想的是政绩立竿见影,一步登天。
要在高校行政化的改革上发力,那么首先就要区分官僚和教授的身份,不过这些年高校内部也发生了相当复杂的变化,比如谁是行政官僚,谁是学者教授,往往已经很难泾渭分明,专业学者往往被抽调去从事行政,而政工出身的官僚,则也往往能混迹为教授博导,大家都在伏地走,焉能辨他是教授,还是官僚?就算是学者出身,一入行政深似海,往往几年不到,要么不堪忍受,回归专业,要么就和光同尘,沾染了一身官僚习气,从此彻底为“官”,不再为“师”了。
就算朱校长如今能重起炉灶,招来一批新鲜血液与精兵强将,但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今日之高校所身兼的非常复杂的身份特征。在西方而言,近代大学的出现,是奠基在独立于政府与教会两股权力的根基之上的,从一开始,大学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由精神的联合体,同样也是新的经济、权力的自由结合体,说成大白话,要有自己的资源与政治地位,才能够排除其他势力的干扰,才谈得上学术自由。而今日欧美大学所形成的学术独立传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私立大学自己筹钱,自然不容政府半句置喙,公立大学虽是政府财政拨款,也要承担公共教育的各项义务,但是一到学术问题,政府行政命令大多便会噶然止步。这种“独立”自然并不是因为西方高校的教授们都有三头六臂,或者个个都是反抗英雄,而是所在社会的权力分散与相互制衡的环境让大学“独立”、教授握权存在可能性。
解放之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国家高度管制的教育形态,高校不仅承担一般性职业教育的职能,还肩负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的政治任务。另外比较微妙的一点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存在的对知识分子普遍的不信任感,所以会利用行政官僚对知识分子加以隐形的管理与约束,因此才会形成如今教授地位低于官僚的荒谬格局。 如今虽然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高等教育的社会化与市场化已经让“职业教育”这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但是高校的“政治角色”从来没有淡化过,反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反而有增强之势。反观我们朱校长,尽管在科大曾经有过“抗命”教育部来抵制扩招的光辉事迹,但是这种靠一己之力所完成的“事业”很难复制推广,毕竟朱校长所要对抗的,不是一所学校的行政化障碍,而是更深层次,也更难以言说的体制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重提民国时期“教授治校”之旧梦,也不过只是望梅止渴而已了。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























![[24小时]空军-夜训遇险_飞行员两避居民区跳伞_20151013112134.JPG](http://dv.dzwww.com/ttsp/201510/W02015101350848045065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