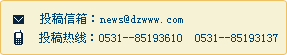中岳嵩山,位居中华大地的中央,号称五岳之尊。在嵩山北麓,有一座古老的寺庙——大法王寺。穿越近两千年的历史风烟,它曾经辉煌一时,引领中国佛教的传播。世纪之交,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令人震惊的佛教圣物,还引出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2001年,大法王寺塔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法王寺在国内学术界日益引起重视,相关研究逐步展开。河南省文物部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决定对大法王寺塔进行保护性发掘。
起初,发掘的对象本来是一号塔地宫。工程进行不久,发现地底下有鹅卵石,防范措施较强。经过研究,考古队于是转而发掘二号塔。
二号塔地宫位于塔基正下方,依次为踏道、宫门、甬道、宫室四部分,总长九米(甬道内共有三道封门墙。)在踏道内发现多枚唐开元通宝铜钱,这成为判断地宫年代的最重要物证之一。
进入宫室前,有一道石刻假门,半圆形的门楣上饰满花纹,左右门扉上各刻有一侍女,头挽双髻,体态丰腴,手捧器物,相向站立。线条优美流畅,栩栩如生。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墓门,宫室内的情景终于显露出来。
地宫里显得比较凌乱,所有木制结构全部腐烂坍塌,但大多数文物依然保存完好。
考古队员迎面看见地宫北部须弥座上,有一具人形坐化像,彩绘袈裟依然可辨。这个包骨像虽然有些残破,但还能看出整个人的轮廓,比如双腿盘坐,双手叠压放在胸前。
地宫内发现包骨像极其罕见,这确切地表明二号塔是一座纪念高僧功德的塔。在佛教界,高僧入葬一般有两种形式,最普遍的是沿习释迦牟尼火化,然后将骨灰装进坛子放入地宫。另外一种是坐化的形式,一般都是高僧,据说高僧去世的时候,坐在那里不会倒。所谓坐化,表示这个僧人功德圆满。像这一类僧人,在入葬的时候,是把真身放在那儿,上面糊一层泥,把他的真身包起来,作为一种葬制。这就是后来形成的包骨像。
这座泥塑包骨像,是河南省唯一一处经过科学发掘的唐代高僧真身像,具有极高的考古学和宗教学研究价值。
□大法王寺二号塔地宫清理出土了铜器、瓷器、陶器、玉石器、蚌器、琉璃器等20余件文物。虽然数量并不多,但几乎每件都是精品。
鎏金铜炉,一出现便令人赞不绝口。它由炉盖和炉身组成,炉高三十八厘米,盖直径五十厘米。整个造型厚重沉稳。通体鎏金纹饰繁缛华丽,有牡丹纹、宝莲纹、云龙纹,还有各种瑞兽,口衔灵芝,足踏祥云,形态各异。虽然埋没地下千年仍熠熠生辉。
鎏金铜炉出土时,炉内还有残余木炭灰烬。它的用途便是“焚香礼佛”。
还有一件青铜文物形状奇特,瓶颈细长而鼓腹。它通高只有十几厘米,可放于手掌中。
铜净瓶也是佛教用品,一般观世音菩萨都手执净瓶,有一个手拿着柳枝。佛教讲究西方净土,佛教里面还有一个净土宗,净瓶里面流出来的都是净化凡尘的一切烦恼,使大家能够理解佛教的奥义,因此观音菩萨就拿着来普降甘霖。
在出土文物中有较多瓷器。在十件白釉瓷中,还有一件黑釉瓷,十分引人注目。按说唐代烧造的黑釉瓷并不多见,其质量水平并不为人所重,但地宫出土的这件黑釉瓷却让人赞叹。
黑釉也是唐代黑瓷中间的佼佼者,它造型非常精美,比较矮胖,带着唐代这种浑圆、大气,而且釉色也非常光亮,是非常少见的。
地宫中出土了五个大小不一的黑钵,它们形制、胎质、色泽均相近,像是一套用具。起初,人们一直认为它们是用黑陶做的普通陶钵。但是,有学者仔细观察后,得出另外的结论。
钵是和尚和僧侣用来吃饭的东西,一般都是青瓷、瓷器或者陶器,但这个钵是用漆做的,漆做钵当食器,只有汉代才流行。这个漆钵一般人是用不起的,普通的僧侣都用陶,这个漆钵肯定是高僧用的。
漆钵与陶钵瓷钵相比,它轻而结实,不易破碎。僧人常携带它云游化缘。久而久之,高僧使用的衣钵,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嗣后代代相传。这个漆要一层一层地上,起码得十几层才能做出一个漆钵。出土的漆钵不会是唐代的,也不会是南北朝的,应该是汉代传承下来的,一代一代的高僧都使用它,传承到唐代,最后可能就进入地宫了。
大法王寺二号地宫的发掘历时两个多月,获得丰硕的成果。人们惊叹于地宫出土文物的精美:地宫内出土文物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有二十多件被评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数量占到全部出土文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种情形在考古界是相当罕见的。
□由于大法王寺地处偏僻,为了防止文物出现意外,工作人员连夜将文物登记造册,准备送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临行前的那天早晨,出于高度的责任感,当时的考古发掘领队最后来到现场对泥土进行筛捡,结果,又有了重大的发现……
谁也没有料到最后一天还会有收获。这是一个古代侍女形象的玉石盒,人首鸟身,头梳高髻,作吹箫状。非常奇特,极富想象力。它整体并不大,长不过五厘米左右,在地宫里被腐烂的木板尘土覆盖,难怪之前没有被发现。
起初,人们不清楚它是何种器物,有何用途。但从它的质地上看,精通玉器的专家却震惊于它用料之珍贵,做工之精致。
玉石盒制作的相当精美,线条非常流畅,雕刻的羽毛、头上的发髻、人物的形态,所有的线条都是标准的唐代工艺,而且刻得相当细腻。在头发丝上的线条加了绿彩,头发加了黑彩,但是这些彩在线条里面,没有到线条外面,证明制作的时候是相当考究的,像这样的工艺,也只有盛唐时期才有。
经过查阅佛教经典,学者终于弄清这个“人首鸟身”玉石盒的名称,原来叫作迦陵频伽盒。
“人首鸟身”是喜马拉雅山的一种神鸟,它以美妙动听的声音被佛经认为是美音鸟、妙音鸟,在佛经的形象里面,它就是人首鸟身,它飞翔在西天的极乐世界,使极乐世界充满欢乐。法王寺地宫里面这个鸟,作为佛族舍利的舍利盒,就寓意着佛仍在西天,它仍然在西天的极乐世界。
学者们查证迦陵频伽在我国的出土情况,发现只在 2009年11月,宁夏的西夏皇陵曾经出土了很多迦陵频伽鸟造型器物。但它们是作为王陵房屋上面的陶制构件,寓意着皇帝的灵魂永在西天灵山。据此,学者们认为迦陵频伽盒的用途,除了作为供奉佛舍利的玉棺别无二用。
玉棺是相当神圣的,只有皇宫贵族和至高无上的佛才能使用,一般百姓、达官贵人、高僧僧众都是没有资格用的,这是封建王朝的礼仪制度,是佛经、佛教的规定所决定的,它出现在大法王寺的地宫里面,绝不是偶然的,它摆放的位置断定它是放佛祖舍利的玉棺。
迦陵频伽盒的出现,印证了大法王寺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建造的最早佛寺之一的辉煌。时隔千年之后,大法王寺重现佛教圣物,对于这座古老的寺庙而言,意义不亚于新生。
然而,围绕着迦陵频伽盒尚有许多疑问待解。迦陵频伽盒的发现位置,处于坐化高僧包骨像的正前方。按照礼佛仪规,高僧死后没有资格供奉迦陵频伽盒。为什么会在高僧塔的地宫中出现这样的佛教圣物呢?这位高僧是谁?是否是在以自己的肉身,于死后化作对圣物的虔诚守护呢?
大法王寺二号塔至今令学者们感到奇怪的是,二号塔及其附近的另两座墓塔,塔身上面的塔铭全部消失了。从现场痕迹上看,明显是人为磨灭的。通常来说,高僧圆寂后盖塔纪念,塔身会有塔铭,记录其生平及功德。
什么年代,什么人,为何原因,故意抹去了大法王寺塔铭上的文字呢?
□正当人们疑惑难解之时,一块神秘墓碑的出现似乎解开了这个谜。
碑文大意是讲在会昌法难之际,为了保护佛骨圣物,两位高僧将其移藏于二号地宫,为防后人遗忘而立此碑文。简短的碑文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想: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僧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极秘密地将圣物转移。关闭地宫之际,一位年迈高僧愿意舍身涅伶,化作圣物千年的守护者。其虔诚殉教之心令人慨叹!
据调查,这块墓碑于十多年前,由大法王寺一位法师发现于二号塔附近。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墓碑长期被弃于一角落而不为人知。多年前,那位老法师圆寂。随着大法王寺考古发掘的进行,这块墓碑终于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些学者对墓碑所记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墓碑上提到的会昌法难,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公元九世纪,唐武宗于会昌年间实行灭佛政策,在全国拆毁寺庙和佛像,僧尼全部还俗,不从者捕杀。当时另一个著名的寺庙陕西法门寺供奉的佛骨舍利被抛洒于地。会昌法难之后,关于大法王寺的记载再不见提到舍利,人们推测,很可能大法王寺舍利塔供奉的舍利也毁于那次劫难。
□拓片上显示落款人是两位高僧:圆仁和天如。对于天如,人们一无所知。有人猜测,天如是否就是那具包骨像呢?而圆仁这个名字,却让学者们为之震惊。
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遍查了唐代的高僧传和续高僧传中,发现中国僧人里面没有叫圆仁的,唯一就是日本来华求法的圆仁和尚。
围绕这个重要发现,学者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圆仁,历史上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的日本著名高僧。圆仁早年在家乡大慈寺,受唐代鉴真法师东渡日本传法的第三代弟子广智法师剃度出家,受到了良好的中国文化和佛教气息的熏陶。
圆仁的时代,唐朝已是整个东方佛教文化的中心,也是日本僧人们向往的文化大国。在日本佛教史上,有著名的"入唐八家"--八位入唐求法的高僧大德,圆仁就是其中一位。公元 838年,圆仁以请益僧身份加入日本国派遣的第十八次遣唐使团。
圆仁在中国行经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七省的广大地区。他把将近十年的见闻经历用日记体裁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全书共四卷,约八万字。书中述及我国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平民生活和中日关系等许多方面,是研究我国唐史的珍贵资料,日本学者称其与《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记》并称为古代"东方三大游记"。
然而,圆仁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却一点没有提及挺身保护舍利的事。
这显然是一桩历史悬案。不过,对日本高僧圆仁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却倾向于肯定推论。
不过,也有研究者提出质疑:圆仁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一部分为回国后补记,为什么他仍然没有提及这个事件呢?
因为中日间的交往,日本遣唐使的往来很频繁,官方组织和民间自发的前往大唐不乏其人,僧侣、官员、商人、社会名流,如果他记了,很容易泄密,传到唐王朝中间,那么嵩山法王寺这批僧人罪责难逃,甚至株连九族。
如果说,这块神秘墓碑所记载的情况符实,恰好解答了大法王寺二号地宫为什么会出土如此精美文物的疑问。
由于缺乏史料,千年的历史迷雾一时难以廓清……(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大法王寺,地宫显秘
2010-05-19 09:37:00 作者: 来源:大众网—大众日报
 |
|
大法王寺寺景 |
 |
|
大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发掘现场 |
 |
|
大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出土的鎏金铜炉 |
王琳

相关阅读
您对其他相关新闻感兴趣,请在这里搜索
> 进入微博< 热点图片
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
2、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大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3、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大众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
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