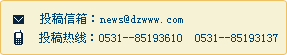□陶唯倩
我在父亲的小院里种下一棵树,我把它命名为:感恩树。
自从四年前母亲病逝后,父亲就日渐苍老。他的老宅被划在隧道拆迁区内,红线一天天逼近。为此,父亲忧心忡忡。远在美国的弟弟打来电话,要把父亲接去养老。电话里,父亲装出欢喜的样子,私下里却跟我说:“我在美国住过一年,一点都不适应!看不到报纸,吃不到家乡菜,电视也看不懂,一日三餐都是比萨在微波炉里转一转。你弟弟说,美国空气好,我老都老了,要那么新鲜的空气干吗?我只想有几个谈得来的老伙伴,每天在公园里转一转,过得舒坦自在。”闻听父亲此言,我心里却是窃喜的。
一直觉得父亲没有喜欢弟弟那样喜欢我,尤其是我们姐弟俩成人后。弟弟读书用功,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后,又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考取医生执照,是国际著名的麻醉医生。而我,高中毕业下放,从此再没进过教室。很多人为了拿一张文凭,去读电大、夜大,我却喜欢阅读的汪洋恣肆和驳杂扬厉,对那种味同嚼蜡的课程不感兴趣。父亲担心我没有文凭难以在社会上立足,有一年夏天,他顶着酷暑为我去“电大”报名,我却把报名表撕了,父亲气得几天不理我。外人问及子女,谈到弟弟时,父亲滔滔不绝;谈到我,父亲只轻描淡写几句带过。
弟弟十九年前去了美国,从此徒有孝心也无能为力。很多个深夜,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把突发急病的父母送往医院;很多个白天,辛苦工作一天,下班了,我和老公还要赶到医院为老人送饭、擦洗——如果父亲去了美国,嘿嘿,这些麻烦事就交给他亲爱的儿子了!
今年6月,弟弟回国探亲,准备带父亲走。护照、签证办得十分顺利,父亲的眉头却越结越紧。他总是在家里清理东西,把一个个包裹捆紧,又重新打开,好像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又好像去了就永远不回来的样子。我有两个晚上回去陪他,听见他在隔壁房间唉声叹气。清晨,他起床去买早点,把早点放在母亲遗像前——母亲走了四年,每天的早点都是父亲换着花样买回来。每当我要出差或弟弟回国探亲讲学,父亲就虔诚地在母亲遗像前烧香:“老太婆,孩子们要走远路,你多多保佑他们,风和日丽的,别出意外啊!”母亲好像听得到父亲的恳求,我和弟弟每次来去皆顺利,很少有班机误点、火车延迟的事情发生。看着母亲遗像前的早点,想着父亲烧香的样子,我眼睛发酸:父亲走了,家没了,谁来给母亲买早点?谁来保佑我们从此一路平安?
那个晚上,我几乎一夜未眠。我想起小时候,每天幼儿园放学,我站在栅栏前,眼巴巴盼着父亲来接我。有一次父亲下班晚了,想着我一定焦急哭闹,他狠命蹬自行车,不小心撞在一块石墩上,跌破了额头。初二那年暑假,我的脚被开水烫伤,父亲天天背着我去医院换药,一个夏天,父亲的汗衫总是湿漉漉的。我下放在农村的那几年,父亲坚持每个星期给我写一封厚厚的家书。在信中,父亲并不讲很多的大道理,只是提醒:你还年轻,不要荒废,有时间多读书;女孩子独身在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每当乡邮员的自行车铃声响起,我冲出去拿过信,迫不及待撕开,看见“倩儿如晤……”几个字,泪水就情不自禁淌下来。有一年父亲出差,回程路上领导说:“顺便去看看你女儿吧!”父亲高兴极了,在小卖部买了大包零食。我住在山腰上,父亲在山底下就大声喊我的名字“姑娘姑娘我来了!”我惊呆了,冲出房门——父亲正大步流星往山上飞奔!
父亲曾经年轻过,曾经健步如飞过。如今他老了,步履蹒跚了,不能让他没有家吧?
想到这些我潸然泪下。我走到父亲身后,对他说:“爸,你不想去,就不去了,跟着我们过吧!我们为你养老送终。”父亲转过身,惊喜得连连点头。
弟弟回了美国,父亲留了下来。我在我的新居旁边,为父亲买了一套小房子:45平米的一室一厅,前后花园。站在我家阳台上,能清晰看到父亲的小院。交房那天,我在花园里种下一棵树,我把它命名为“感恩树”:铭记父母恩情,感谢父母养育。
感恩树
2010-08-05 15:15:00 作者: 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王琳

更多新闻
相关阅读
您对其他相关新闻感兴趣,请在这里搜索
> 进入微博< 热点图片
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
2、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大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3、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大众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
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